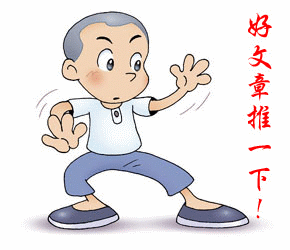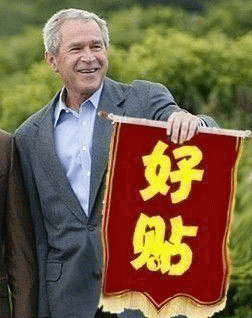2010�~�v�Ĵܭ����i�����ꤧ��-�����j��
�ܦh�ɭԧڭ̬O�H���֦��������Ӥ��O�H���O���������ҹ�ۨ����s�b�C�O�H�H�ڭ֦̾��h�j�����B�h�ֿ��B�h�j���Фl�A�Φ�����s�骱�N�A�ӵ��P�M�Ŷq�ڭ̡C�o���O�D�`�������A�]���H�����ȱN�|�ܱo�D�`����ơC�ҥH�ͦӬ��H�A�S�O�b�ثe�o�ӮɥN�A����o�Ӱ��D�q�o�ӱo���n�C
�������O�A�b�Ȭw�ܦh�a��A�γ\�b����]�@�ˡA�ڭ̴X�G���N�a��ѥj�Ѫ����z�C�Ҧp�b�L�סA�̦a�۷����H�L�R�C�ڬ۫H�A�̤j�����D�̦a�C�p�G�n�D�X�@�ӧ����H�������v�A���ӬO�L�C�L�D�n���H�������O�L���D�ɤO���z���P���ǡC���L�A�ڤ����D�A�̬O�_�M���L�o�ӫD�ɤO���Q�k�O�q���̨Ӫ��C�L�ƹ�W�O�q��ù�M���������A�@�Ӭ���H�M�@�ӫX��H���̱o�Ӫ��C�A�̪��D�o��ӤH�S�O�q���̱o��o�ӷQ�k���O�H�L�̬O�q�L�ױo�쪺�C�u�����~��H�}�l���`�ڭ̪��j�ѻ����[�M���z�ɡA�ڭ̤~��M�y�\�d�N���̡C
�H�ʪ����ȡA�p�H�A�q�ӳ��O�D�`���n���C�o�O�\�h�p��гo�˪��F�贼�z�����ߥD�D�C���ɭԧڭ̷|��o�ǥj�Ѫ����z���@�O�g�H�M�L�ɪ���Q�A�ө������̡C�o���O�i�H�z�Ѫ��C������O�H�]���Ѧp��гo�˰��j�����z�ܤ����`�`�O�H�ݰ_�ӴI�t�v�Ц�m�������P�H�x�Ÿ��ӧe�{���C
�|�Ҩӻ��A��Ы�Q���֤P�D�����@�O�O�d�C���G�ڭ̴N��O�d���@�O�@��ܷO�����B�ܩv�Щʪ��B�ܦ��q���欰�A�M��פ�A���A�`�s�C�o�O�D�`�������C�O�d�X�G�`�O�Q�������X�a���~�|�����ơA�q�S�Q�L�@�Ӥh�L�i�H���O�d�A�Ϊ̤@�ӬF�Ȥ]�i�H�ѻP�O�d�C�q�S�Q�L���Ǥj�Ȧ檺�`���̥i�H���O�d�C�p�G�o�ǤH�A�ר�O���Ǥj���~���`���̡A�i�H���@�B�I��O�d�A�o�Ӫ��|���ȥi�H�M�ӡB�M���B���ͺA�A�ڭӤH�{���L�̪��ͷN�]�|�\�C
���ڭ̽ͨ�O�d�A�ڭ̴X�G�`�O�p�Q��@�ǫܦw�Ԫ��e���A�n���[�����ķO�طL���C���ڦb����s�@�v���ɡA���H�ݧڳ̳��w���q�v�O���@���A�ڻ��O�m�ѥͱ��H�g�n(Natural
Born Killers)�A�ڨS���b�D�]�]���O�ɦb�}�����C�o���q�v�ܤ��٬O�ڳ̳��w���q�v���@�C�p�G�A�ݬݳo�����l�N���D�A���ƹ�W�Z�ɤO���C�i�O�A�ݡA���A�ۦb�q�̤[�F�A�C�ѩM�@�Ǭۻ��ũM�����ġB���H�̲V�b�@�_�A�A�N�ɦV��ѰO�ۤv����L�ѩʡA�ɤO�B����M�g���C��ڦӨ��A�o���q�v�i�D�ڡG���M�ڱq�X�Ͱ_�o�@���l��������Ю{�A�ڬO�������,���ڨ�ƥ��������A�i�H�H�q�v�̪�����@�˼ɤO�C
�s��X�{�����N�h�W���@�N�O���ۧڲ������A�]�]���ڭ̧ѰO�F��L�H�h���O�d�C�ڭ̬Ʀܳs��ۤv�����O�d�A�]�����o�Y��ۤv������A�ҥH�ڭ̥����֦��n�߸��B����•�µn�B�j���o�ǰ��~�����U�ڭ̪Y��ۤv�C�����H���A�ڭ̥û������o�طQ�n�A�Ѧۤv�B����ͩR������C�ڤ����D�o�˪��{�H���S���b����o�͡A�i�O�b��観�ܦh�C�֦~�۴ݳζ˦ۤv�A�Φۤv���L�B�ۤv����C���ڰݥL�̳o���z�ѮɡA�L�̦^���u�O�Q��P���ۤv�C��ڦӨ��A�o�O�ܲ`�誺�A�]���o�ǫĤl�̨S���o����ɡA�����D�P���ۤv�����T�覡�C�L�̰ߤ@���P���覡�N�O�z�L�Y�ب�E�A��E�H�ι��E���I�g�C
�t�@���ڷQ�M�A�̤��ɪ��q�v�O�m�V���y���H�n(Deer Hunter)�C�ڷQù�B�S•�w���S�O�Ӥ����t���C�ڬ۫H�A�̦��ǤH�ݹL�o�����l�C�o�����l�ƹ�W���ڮ��I�F�n�X�ѡA���ɭԧڥu�n�@�Q��o�����l�A�N�S�|�߱��C�g�@�}�l�C�ڹ墨���Xù�����L�䪺���Y���z�ѬO�A���ӤH�W�O�Q�۱��A���ب�E�ι��E���I�ĬO�o�j�Ӧ��O�C�ڷN�Ѩ�ڥi�H�����a�A�D�`�����a�V�W�o���}�C���A���ʺj�W������A��ۤv�}�j�A�j�̦A���S���l�u�A�A�ߨ�P���쬡�۪��O�q�C���ڭ̿�ѤF�j�Ѫ��D�~��p��боɧڭ̡A�P�䪱�Xù�����L��A�ƹ�W�ڭ̥i�H�z�L�ܳo�M���A����|�ͩR���O�q�C
�b�ڰ���f�Y�a�e�����A�̶}�l�o�ݤ��e�A�ڷQ�A�P�j�a���ɤ@���q�v�C�ڥ������@�ǻP��k���������e�A�ܩ�p�ڤ@���b�q�v�C�A�̬ݹL�m��窺�����n(Taste of
Cherry )�o���q�v�ܡH�o�O���ܬ����q�v�A���z�@�ӥ���M�u�����H�A�Q��@�ӤH�i�H�b�L����I���L�C�L�Q��@�ӤH�@�N���L���ӧ|�A���o�ӷQ�۱����H�쨺�ӧ|�̪A�r�ۺɡA�M�ᨺ������A�_���W��X���N�L�I�F�C�L�N�O�n��o��ӤH�A�i�O�S�H�@�N���C�H�̤��O�Ӧ��A�N�O�����L����n�o�C�̫�L�ש���@���@�N���L���H�C�o�ӤH�ݨ��ӭn�۱����H�A�A�u���T�w�n�o�ܡH�M��o���@�N�������H���F�@�ӬG�ơG�L��O�@�W�x�H�A�]�L�k�A�Ԩ��U�h�A�L�N�b�@������W�W�Q�A�i�O��F�_�F�A�L�N�S�����C��O�L�N�Y�F�@�����A��窺�����q�ӨS���o��n�Y�L�C���M�L�H�e�Y�L�ܦh�����A�i�o�O�L�Ĥ@���u���~������窺�����C���M�A�ڤ��|��q�v�������i�D�A�̡A�A�����Ӧۤv�h�ݳo���q�v�C
���I�����o�ӦW���w�g�Q�ݥΡC�ڭ����ӧ�o�ӦW���令���������C�]���L�פT�����B�������A�b�I�ת����q�ɶ��̡A�A�b���ۡA�A�O���N�Ѫ����۪��C�ثe�A�ڭ̰W�O��ͨ��סC���ڭ̳ܯ��ɡA�ڭ̦b�Q�ۧO���ơF���ڭ̬ݵ۬��R�����ɡA�ڭ̪`�N�����������C
���۫ܭ��n�A�i�O���r�r�����ۧn�C���A�o�ɡA�ڷQ�O�d�N�Ͱ_�C�ڤ@���b���O�d�O���@���A���O�M�ݩH�M�v�ФH�h���C�o���٦��@���q�v�ڷQ�ͽ͡A�ЧA�̥h�ݤ@���w��q�v�m��ť���ɡn(The Life of
Others)�C��ڦӨ��A�o�O���@���̴Ϊ��q�v�C���ڬݳo���q�v�ɧڧ����a�ĤJ�@���A�ӧѰO�n�����L�C�ڽL�ۻL�b�v�|�̬ݧ��㳡�q�v�ѤF���L�C���q�v������A�ڦ]���L�ӳ¦Ӥ[�[�����_�ӡC�o���q�v�O����ڭ̳q�`�{�����Ҧh�i�c�A�i�O���@�Ӷ��Ҧh��O�d���G�ơC�n�F�A�ڤ��A���Z�A�̤F�A�аݧڰ��D�C�аݥ���A�̷Q���D���A�ڷ|�ɤO�^���C
�ݡG�ڱq����߹L��k�A�����ܦh�ðݡC�ڦ��b�s�[�Y�A���̪������A���u�O��Ъ��A�٦��ѥD�СB����Ъ���¾�H�h�L�۰��ت��ͬ��C�ڱ`�`�ݨ�L�֦̾��_���B���h���A�٦��ܦh�ݥΪ�������D�C��ı�o�X�a�����ӱq����ͬ����X���C�ڤ����D���i���p��ݳo�ǨƱ��A�L�̬���|�o�ˡC
���G�o�O�@�ӫܦn�����D�C�o�O�Ҧ����F�Dzγ̤j���D�ԡA��Ф]���ҥ~�C
���쩳�A�ڷQ�o�O�ӤH�ۤv���M�w�C���O�ڭn�i�D�A�A���A��ЩM��Ю{���t�O�O�D�`���n���C�]����Ю{�O�H�A�u�]���L�̦b�ײߦ�k�A�ä����ܥL�̤@�]�����N�|�ܦn�C�o�N�����D�M���D�ҭ��@�ˡC
���ڧi�D�A�@������D�W���ߪ��C�o�O�@�ӫܭ��n���D�D�C���A�R�c�ɡA�A�ܤ֥i�H���D�o�c�O�q�j�Q�����٬O�����C����M�F�������Ʊ������ܦh���P���`�סB��ij�B�覡�h�P�������u���C�o�O�D�`�ӤH�ƪ��A�]�]�����F�ʥͬ��x�������C�@��Ө��A�p�G�A�ݦ�Ъ��ХD�O�֡A���O���{�ȥ���C�L�O�Ӥ^���A���O�L�L�����覡�C�L�S���_���T���A�u���@�Ӥ^�Q�Ϊ��ڡC�i�O�p�G�A�̩�o��²��ӵ��w�@�ӭצ�̡A�p�S���_�����B�����סA���]�i��D�`�~�ɡC���ܦh�H�ݰ_�Ӧ��G�ܯ²b�B��²��B�D�`�X�@�����A���L�̦ۤj�]�ڰ��^�B�g�ơ]�ںC�^�A�D�`�ۨp�C�L�̬O�S�Ϊ��A�ڤ��p�M�����Ѥj�b�@�_�C
����惡����ѨM��סH�ƹ�W����ۤv���F�@�ӵ��סC�L�@�ӦA�A�ӤT�a���A�ӬݬݡA�Ӥ��O�A�ӥ[�J�C�@�ӤH������ť�D�M����B���R�D�~�B���R�Ѯv�A�M��~�l�M�o�����C�o�O�L���ѨM��סC��ڭ̦Ө��o�ä��e���A�]���ڭ̳��ܿ��ġA�ڭ̳��Q�n�����|�A��O�ڭ̴N���J�����C�ڧi�D�A�A�b�Ҧ����������A���F�������û����|�˳��C�ƹ�W�A���Ҧ���L���g�٬��ʰI�h�ɡA���F�����@���W���A�]���ڭ̨C�ӤH��ı�o���w���C
��:�����ڷQ�P�±z���}�ܡC�ڨӦۤW���C�ڷQ�n�аݤ@�ӱM�~�����D�G�b�m�����n�o���Ѫ��e���̡A�z�g��Z�O�۫H�|�k�L���H�N�O��Ю{�A�ӤZ�O���۫H���N���O�C�ڷQ�n�бz�ѻ��o�|�k�L�����b����C
���G��A�o�N����Ū�㥻�ѤF�C�n�a�I�ڴN²�u���ͤ@�U�C���]�A�O�@�Ӧ�Ю{�A�A���B�ͰݧA��צ�k�A�A�۫H���O����C�A�`����A�@�A�ڭ̬۫H���O����C�o����C�o�O�H�Ϧ���D�i���A�]���L�����Ӭݬ����A���O���ӥ[�J���C�Ϊ̧A���A�@�A�ڭ̦�Ю{�۫H�I�w�A�o�]����A�]���L�ױФ]�I�סA�{�b�ܦh���P�ži�ͤ��ߡ]spa�^�]���C�ҥH��Ш쩳�O����H�N�O�o�|�Ө��a�A�A�����֦������A����u���T�ӿ�|�@�ӡC�@���y�@�B�M�X���ƪ��ҵL�`�]�Ѧ�L�`�^�A�o�O�@�ӡF���۵L�����@���B�Ҧ��������O�W�]�Ѻ|�ҭW�^�F����ƪ����~��A�p��l�B�Ȥl�A����ƪ��~����{���ä��O��������]�Ѫk�L�ڡ^�F�Ү��O�W�V����]�I�n�I�R�^�C�N�O�o�ǡC
�ݡG�ڷQ�n���D���̪����b��A���O�����C
���G�n�ڡI�p�G�A�i�H�M���G�סA���|�e���ǡC�Ĥ@���A�A�����o����ܡH
�ݡG�O���C
���G�ĤG���O�H
�ݡG�]�S���D�C
���G�n�A�֤F�I�{�b�ĤT���C
�ݡG�]�S���D�C
���G����A�ĥ|���C
�ݡG�]�S���D�C
���G���A�����D�b���̡H
��: �ڪ����D�O�G����O�즳�j���z���H�A�L���|�u�O�H�N�a�|�X�o�|�ӱ���A�o�����̤����S�����p�A�N���A�̥����۫H���̡C���̤����@�w�����b����C
���G�@�I���b���Y�A�ک��դF�C�o�O�@�ӫܾdzN�ʪ����D�A�ܦn�A�D�`�n�C�@���@�ӧ���z�����o�ǽ��I�A�X�ۦn�X����g�C�b�j����g���A��p�m�k�ظg�n�]White Lotus
Sutra�^�A�ڬ۫H���媩���A�ں٥��@�m���Y�g�n�]Flower
Ornament Sutra�^�M�m�����g�n�]Lankavatara Sutra�^�C�b�o�Ǹg��̡A�A���ɥi�H�b�@���g�Ѥ�Ū��Ҧ��o�ǽ��I�A���b���P���a��A������L�\�h�оɡA�A�Ҧp���L�`���}�ܴN�O�䤤�@�ӳ̬����n���C
��A���b��A�{�b�ڲz�ѧA�����D�F�C�q��K���q�������A���ڭ�����@�Ӹg���ɡA�`�O����ӭ��V�C�ä��O�������ơA�ӬO�@���@�ӰQ�ת��u��A�C���ڭ�����@�ǨƱ��ɡA�û�������ӭ��V�ݭn�h�˵��C�|�Ҩӻ��A�A�M�ڤ@�_�ݵ۳o�ӡA�ڷQ�A�ڳ��|�P�N�o�O�@�i��l�C�i�O�p�G�@����L�b����̳Q�����a�N���F�A�o�ɧA�ڷ|�Q�줰��H��������l���N���|�X�{�b�ڭ̪������̡C���ӥN�����A�ڭ̷|�{�w���O����C�ҥH�C��Ƴ�����ӭ��V�G������{���B�H�Υ������C�������A�۹�u�z�]�@�U�͡^�P�s���u�z�]�Ӹq�͡^�C���̬J���O�������]���O�X�@���A�i�O���ڭ̽ͽɡA�o���o�����}���A�_�h�ڭ̴N�S��k���q�F�C�ҥH�b�o�|�ӯu�z�����A�e��ӬO�۹�u�z�A���ӬO�s���u�z�C�o�N�O���̪����b��C
�ݡG�ڤ��P�N�o�ӻ��k�C�ڥi�H�D�ԶܡH
���G�i�H�A�i�H�A��C
�ݡG�ڬO�o��z�Ѫ��C�|�k�L�Q�ת��u���@�ӯu�z�A�s���u�z�C�ڭ̽ͽת��n��O�ߤ߭n��O�ߪ��A�i�O������w�W�V�o��̡C�@�ӤH�i��|�H���o�O��l�B���l�B�H�A�ξ�Ӻϳ��T��s�b�C������o�dz��O�۬ۡC������H�]�����̬O�X�M���C�S���@�˨ƪ��O�W�ߦs�b���A�ҥH�L�����Ѫk�L�����A�Ѫk�N�O�@���{�H�A�L�ڴN�O�S���@�ӥD�_�C�ҥH�o�N�_�w�F�ڭ̰��۪����ӥ~�b���ۡA���Ǭ۳��O�S���ۧڪ��A���s�b���A�ҥH�����n���ۡA�o�O�Ĥ@�h�N�q�C�M��A�ĤG�ӽͽת��O�{�H�Ѧ�ӨӡA���ͪ��O�{�H������C���̱q���̨ӡH�]�����ӥ\�ΡA�ӳo�ӥ\�Τ]�O�Ӥ۬ۡA�ҥH���ͪ��O�L�`�C�b���i���ۧ@����Ķ���̡A�ĤG�Ӫk�L�ȫ������A�i�O��ı�o�����u�O�䤤���@�p�����A����ڤW�]�t�Ҧ����믫���ʡA���B���B�a�B�ŵ����C�Ҧ����\�γ��O�L�`���A�]�ӾɭP�h�W�C
(½Ķ�H���z�M���D)�L�{���o������A�Ĥ@�����ӬO�L�ڡ]�Ѫk�L�ڡ^�A�M��O�L�`�]�Ѧ�L�`�^�A�A�O�����]�Ѻ|�ҭW�^�A�ĥ|�ӬO�I�n�]�I�n�I�R�^�C�ӥB�u��������O�I�n�C�i�O�]���ڭ̤����ճo�ӹD�z�A�ҥH�ڭ̦��h�W�C�Lı�o�o�O�u�z�A�ӥB�L�Q���D�o�˪����b��O�_���T�C
���G�ڲM���F�C�O���A�o�Ƕ��Ǥ@���b�ܡC�L�N�Ѩ�o�I�u���ܦn�C�ڨ��|�X�ӨҤl�C�ڭ̦b�Ͷ��ǡA�o�|�Ӫk�L���зǶ����`�O�w��@��������C��@������Ө��A���Ӳz�ѵL�`�O����e�����A�]�����O�i�H���Ҫ��C�M��y�L���@�Ǫ��O�����A�M��A���@�I���O�ũʡC�̫�@�ӬO�������C�A�һ����S������C�ƹ�W�A�b����G��k���ɡA�L�O�o��оɪ��A�����L�ڡB�ũʡC�N��b���ѡA���ڭ̱б¦�k�ɡA�]�O�n�ݨ������C�p�G�A�b�Ǫk�ɹJ��@�Ӥ������o���ǥ͡C�o�N���ۤ���H�o���ܳo�Ӿǥ����o�p��ݰ��D�G�o��ڦ���v�T�H�ڥi�H�o�줰��H�o�O���o�����H�A�]���@�Ӧn���ͷN�H�@�w�n�����D���Q���A�L�̤~�|���o�ΥͷN�A���M�O�H�I
�o�N�O����٧@�j����С]Mahayana�^�AMaha�O�j���N��A��s�j���n�_�ߡA��դj���A�סA�ҥH�A���оɪũʡC���M�A�٦���L���k���C�H�j�꺡���ҡA��L�̦Ө��A�L�ڴN���O�Ĥ@�쪺�A���M�]���O�L�`�A���M�]���O�����A�ӬO������I�n�C�L�̭����ͪ��N�O�I�n�C�ҥH���ǬO���@�˪��C
�ҥH�|�ؤ��P���H�ӡA�L�̥i�H���ܶ��ǡC���u�O�|�ءA�O�X�Q�U�ؤ��P���H�C�����Ъk�O���F�ݭn��L�کM�I�n��b�@�_���H�C�]���A�m�j�øg�n�]Tripitaka�^��110�U�A���M���O�X��o�ӭ�]�C
�ݡG�q�`�ڭ̳��ͤT�k�L�C�ڬO�Ĥ@���q���i�����Ѹ�Ū��|�k�L�C�ڷQ���D��]�C
���G�ܦn���[��C�ĥ|�k�L�]�I�n�I�R�^�u���O�������C���ɲĤT�Ӫk�L�i�H�]�t�@���A�@���ҪšC�A�����A�T�k�L�]�����P���Φ��C�ҥH�A���Ǧ�g�̴N�S������I�n�O�W�V���ݪ� (�I�n�I�R)�C
��:�Ѻ|�ҭW�O?
��:�O���A�]���ܦh��L����g�S������Ѻ|�ҭW�A�]�����]�t�b�Ѧ�L�`�̡C�i�O�]���@�Ǧ�g�u�����Ӫk�L�C�ҥH�o�N�O�ҿת��X�i���κ�²���C�o�O�@�ӫܤj��ij�D�A�@�ӫܤj�]�ܭ��n���dzN��ij�D�C
���H�γ\�|�ôb�A����n�˱o�o������C����Ү�����A�L���o�ӯu�z�O�L�k�DZª��A�N�⻡�F�A�]�S�H�nť�A�L�٤��p�d�b�˪L�̡C�ڤj�x�a�q���A�o�ܶH�Ѥl�������D�i�D�D�`�D�A�W�i�W�D�`�W���C��ӡA�]�����D�`���n���\�w�D�ШD�A����~�}�l�Ǫk�C
�j���@�ʦ~�e�A�@��D�`�S�O�����þǪ̮ڴ��s���A�L�ӯS���F�A�H�P���Ϊ����äH�������L�A�ӥB�N�L���i�ʺ��C�L�]�O�m���g�n�]The Karma
Sutra�^�@�Ѫ��@�̡C�L�����A������оɬO�o�˪��G�p�G���H���j���ۧA�A�G�A�����j�����ӤH�O���A�A�|�������M�A�A�O�����C���ӫ��j���H�H������A�����O�߸̸ܶܡH�٬O�u�O�L�W�����H���A���M���|���ڥu�O�L�W�����A�ڮڥ����o��Q�C�A���M���|�o�A�o���G�A���ʩR�C�ڴ��s�����A����Ҧ����оɳ��O�X��L���O�d�A�]�����O��L�H�@�Nť�����e�P�覡�A�Ӥ��O�]���L�Q���C�o�O�@�ӫD�`���n���[�I�A�]��������Ǫk�ɡA���\�h�ݦ����ۥ٬ޤ��B�A�N����²���M�X�i���@�ˡA�o�O�]�������P���������͡C
�|�Ҩӻ��A����g���G�����ڴ��g�O�@�����Τ@���ߤl�����A���ܦ��ۧڪ��s�b�C�M��b��L�p�m����g�n��������g�̡A�ۧڨä��s�b�A����]�q���Ǫk�C�p�G���Hı�o����ܬ��A�L�N���F�C�ҥH�A�o�O�@�ؤ覡�C�M��A�b�t�@�ӮɭԥL�S���G�߬O���A�ߪ����ʬO��C�o���O���M�P��ť���C�p�G�̤l��ť���O�����_�����A�L�|�ͯI�n�O�W�V���ݪ��C�p�G�̤l�O���_�`�����A�L�N�|�h���@�ǶH�L�`�θU�k�ҪŤ������оɡC
���ó���B�Ǫ̶̭ɦV�_��o�|�k�L���@��Ъ��H���A�]���o�|�k�L�X�G�[�\�F�@���C�o�۷����n�A�]�����p�@����ó���n�@�ӧ̤l�h�q�̥X�a�B�c�Y�B�߱�@�����ͬ��A�p�G���O�]���o�|�k�L�A��Ю{�N�����۫H�Фl�B�a�x�M�Y�v�O���c���C�Ӧp�G��Ь۫H�����c�A��Ӧ�Ъ���t�N�Y��F�C����n�D�L���H�{�c�Y�A�ä��O�]���L���Y�v�L�ӡC
����n�X���A�]���@���B���誺�@�ɬO�Z�����C�O�A�S���A���o���O�̦n�����סC�o���O�A�����X�����D�n��]�C�@�ӤH���ӭײߥX�����D�n��]�O�]���S������i�X�����A�{�b�ڧ�C�ӤH���d�k��F�C
��:�ڬO�q�W���Ӫ��C��ť�����i����m�D�w�g�n������C������H�������������Y�H������b�U�_�ɡA�m�D�w�g�n�ण�����즣�H�����Ӧ�����˪��a��H
���G�ڥ����n�Z�ӧڨèS��Ū�h�֡m�D�w�g�n�A�u�ݤF�@�I�F�٬ݹL�@�I�m���l�n�C�ƹ�W�ڬO�ܶƺC���C���H�e�ڳo�ǮѡA�ڨM�w��b�~�ⶡ�̬ݡC�o�N�O�ڦ��h�ƺC�C�i�O�ݤF�Q���H��A�ڴN�����b�~�ⶡ�ݤF�C�z�I�Ӳ`���F�C���ɷ���Ū�m�y�n�ɡA�ڷPı���O�ܱ`�ѩʪ��C�b��k�̡A�`�ѬO�n���A���٤����n�A�A�ݭn���z�C�M��ڷQ�A�@�A�i�O�Ѥl�B���l�o�ǤH�O�����z���C�N�ڤ@�I�֤��A�ѡA��ı�o���u���i�H���U������|�C�ڬ۫H��L���Ǫ̭̥i�H���A�z�ѳo�@�I�C
�ڤ��ҥH�o�O�]���p�P��L���{�N�ư�a�A����������������ۤ@��è�g�C�Q���B�\��B��ΩʡB���ΡA�Ҧ��o�dz��ܭ��n�C�i�O�ڭ̪��D�n�ت��O�ּ֡A�ӳo�ǪF���ڤW�õL�k�a���A�s�����ּ֡C��ı�o�q�L�\Ū���l�B�Ѥl�M��Ы�Q�A����H�N�}�l�Y�����L���������ȡA�]���L�άO�h��j���Ѳ�C
�ݡG���i���Ӧۤ����A�j�h�ƪ�����H�藍���������A�ѡC�z�i�H���Ф@�U��������жܡH�ĤG�A�ڤ]�Q�A�Ѥ��i�����ǩӡC�z�i�H���ڭ̤��Ф@�U�z���ǩӶܡH
���G�����A�����O�@�ӫD�`�p����a�C���ڥh���J�ɡA�����H����F45�����~��줣������m�C���譼��ЬO���a���v�СA�p�G�ڭ̷����O�v�Ъ��ܡC�����]�������L���������a��A���@���O�Ӭ۷������M�ּ֪���a�C�{�b������M�Q���@�Ѱ�A�s�A�Ů�B�s�r�A�ܱo���@�I�I���n�A�o�藍���i��O��M�I���ơC�ĥ|������O��۷��n���g�D�C�H�̽ͽת������O���W�������A�L�N�O�䤤���@�C�L�W�j���H���������D�A�L�Ʊ�H���֦��v�O�C�ҥH�L�{�b�u�O�W�q�W������C�b�g�D�߾����U�A����ȶȬO�ӶH�x�C
�ڪ����p���@�I�����C��������]�O�A���ӫܩ_�ǡA�Y��ӻ��ڪ��e�@�@�Ӧۥ|�t�A�ӳo�@�@�O�Ӧۤ����C�γ\�A�̤��A�ѳo�O���^�ơC��@����äH�O�@��D�`���n���ơA�L�̮ڥ����Ҽ{�o�Ǯt���C�ڹ�W�r�M��V���@�Ǿ\Ū�x���g�C�ڰO�����W�r�]�`�`�⥪�k�ˤϡC�ҥH���ڲĤ@���H�ҿ���@�������h�|�t�ɡA�J��ܦh�e�@�@���̤l�C�ڤ��ҥH�����ҿ����O�]�����٬O���۫H�ڬO�L����@�C�L�O�@��D�`�F���_���H�A�ӧڹ�ۤv���dz\�A�ѡA�ҥH�ڤ����D�C���`�O�ѰO���ǤH���W�r�C�䤤�@�컡���z���|���O�o�O�H�o�ӦW�r�O�z�����C���ҥH��@��צb���ê��|�̧�t�ۤ@�ӫܭ��n������C
�b�Q�K�@�������ΧA���æ��ܦh���O���D�C�ڷQ�����I�H���a�M�D�a���������t�����C�b���a���D�ɡA���u�r�A�D�a������ΡI���H�̤��A���`�D�a��Q�A�ӹD�a�ǩӴN�ܱo�@�����n�C�b���å�M�A���ܦh���P����Q��t�M���z�ǩӡA�䤤���ܦh�]�����t���D�ӥ��ǡC����•�ܭ�•���i�O�����Ь��B�ʪ��Ĥ@�H�C�L�u�ߦa�L�q�Ҧ����ǩӡA�æb���V�X���P���O���e���U�O�s���̡C�p�G�A�ݧڬO�ݩ���Ӭ��O���A���@�N�o�˦^���A�ڬO�@�ӧV�O�l�H���{�ȥ�����̡C�N�O�o�ˡC
�ݡG�ڷQ�бФ@�Ӧ������z�����D�C��ı�o�ڭ̻ݭn�ܦh���z�ӧP�_�A�Ӥ��O�u�O�[�J�C�o�˪����z�Ѧ�ӨөO�H��ı�o�o�O��x�����ơC
���G�O���A�o�N�O����A�n���h�@�Ӻðݪ��ǮաA�ûy�̥sshedra�C�b�o�ئ�оǮո̩Ҧ����Ǭ���O�G�סC�A�����G�סA�γ\���{�ȥ���O�����C�o�ؤ��J�覡�O�̦n���A�]�����ôb�����A���N�O���z����l�C�����z�����A�v�������A�V�h���ðݶV�n�C�o�˧A�N�|��çA���ðݡA�ӳo�N�Q�٧@�@�q�ߡC�@�q�߬O�A�����n�����A�_�h�A�û��L�k���ơC�p�G�ڷQ�n�p�ѡA�ڥi�H�]��åͶ��h�A��n�X�Ӥp���h�óo�쩳�O���O�åͶ��A���L�P���P�ɧڪ��H�֦b���o�C
�ݡG�ҥH�̱z�����A�@�q�ߨä����P����H�@��W�v���o�ӧΦ��C�z�O�o�ӷN��ܡH
���G�O���A�@�q�ߨä��O�D�n���Φ��A�ƹ�W�h�ä~�O�D�n���Φ��C�p�G�A�h�@�Ӧx�q�A����@��v�����Ĥ@�ѡA�L�N�n�D�A�Z�Ƴ��ӥL�������A�A�N���n�A�^�쨺���x�q�h�F�C
�ݡG��ť���@�ӤH�����C���@�B�Q���Y���A�_�h�N���O�u������Ю{�C
���G�i��o�˪����ܡA�ܩo�˰����ܴN���O��Ю{�A�ڭˤ�ı�o�C�S����g�̦��o�˪��O���C�A�i��|���}�Y�ǬJ�����W�w�A�i�O�p�G�o�˴N���O��Ю{���ܡA����Ҧ����q�l�B�������d�M����H�N�����O��Ю{�F�A�]���L�̤@���Y�סC�Ӧp�G�L�̤����榨����Ю{�A�ڭ̴N�ॢ�F��и̳̤j���@���A�]���L�̬O�e�j�ӥj�Ѫ��C�ƹ�W�ڤ~�h�L���̡A�L�̪���k�оɥi�H�q�H���ǤW�Q�ҩ��O�Ѧ���DZª��C
�ݡG�ڨӦۤW���C�ڷPı���Ѫ��}�ܤ�H�e��ť�L���ҵ{���ѵ��ڧ�h������Ъ����ѡC�ڹ��k�@���ܦn�_�B������B���ˤ��P�C�M�ӡA�ڳo�@�N�H�j�h�ƬO�����_�L���ת���Ƥ��A�]�Ӥ@�Ǧp�@����ì���i�H�è��_���������A�ιF���@���禿�o�ǯ���G�ơA�����F�ڭ̱�����k����ê�C���i����軡����Ǫk�ɬO�̾ڪ���ӶǪ��C�ڷQ���dzo�����G�ƥu�O�H�x�ʪ��A��O��ı�o�ڪ���ê�w�g�M���F�C�i�O�b���i�����Ѹ̤]���쨺�Ӽ��������G�ơC���u���o�ͤF�ܡH�o��ګܭ��n�C�p�G�L�u���è�������A���ڴN�̤F�F�p�G�o�u�O�@�ӶH�x�A���ڪ���ê�N�ư��F�A�ڥi�H���}�ߴv�C�ڤ��O�ܽT�w�A�j�v�A��_�бz���ڸ�V�ڪ���ê�H
���G�o�O�@�ӫܦn�B�ܭ��n�����D�C�ڭ̦b�Q�ת��O�۹�ʡC�|�Ҩӻ��A�p�G�A�@��ѳ��M�A�̦n���B�ͦb�@�_���o�ܶ}�ߡA�u���ܶ}�ߡA�ɶ��N�L�o�ܧ֡C�i�O�p�G�A��M�Q����c�̥h�@�Ӥp�ɡA���@�Ӥp�ɸ̪��C�@���C�@�����L�o�ܺC�C�ҥH�A�]�гy�F�@�ө_��A�]���@��Ѥ�@�Ӥp���ٵu�C
�b���ڭ̻ݭn�A�Ѫ��O�G����b�оɨS���ҿ׳̤p�B�u��s�b���̤p�A�]�S���ҿׯu��s�b���̤j�C�N�s���z�Ǯa�]�٦P�o�I�C��p�A�o�i��l�Ӥj�A�ҥH���Ӥ���p�C�i�O���Ӥ��O�̤p���A�]�����䨺�ӧ�p�C�o�ӯu�z�A�ι�o�ӯu�z���F���N�O�_��C
�o�O�ӫܭ��n�����D�A�]���b�X�G�Ҧ���g���A����q�ӨS���]�I�i�_��ӳQ�g�|�A�D�`�D�`�֡C�N��b���ѡA�ڭ̪��W�v�]�`�`ĵ�i�ڭ̡A�p�G�ڭ̳o�ǧ̤l���@�I�I�����q�B���@�I�I���k�O�A���O�@�ػ�ê�C�ҥH�̩Ԥ�ڹ�Sã�کҰ����A�O�b�оɤj�P�p���D�G���סC���ڭ̻ݭn��S���L�Ш|���媼�ѻ��o�ǹD�z�ɡA�u���z�L�o�˪��G�ơC
�b�����ǧ@�~���A�ڤ@��ı�o�m��C�O�n�O�D�G���׳̤F���_���Ч����@�C�]���ťû��]�S����k½�X�p�Ӧ�x�ߡC�b�L�׳q�L�G�ƨ����z�D�G���ת��DzΤ]�O�ܤ��i��ij���C�b�ۦW�v�֡m���F�Cù�h�n���A�����P�����������L����S�٦��䥦�ܦh�H�A�䤤�]�A�L���Ѯv�A���O�������A���O�L�����o�˰��C�o��Ѯv�O�Ӫ��H�C�o�ǥ��O���H�x�t�q���A���u���n�����O�G�Ѯv�L�k�б§A����F��A���b�۹諸�@�ɸ̡A�@�����O�Ѯv�ұбª��C�u�����A�W�V�Ѯv�ɡA�A�~��F���C���L�A�ЧA�̤��n�����ۤv���Ѯv�C
�ݡG�ڷQ�n�бФ��i���A�z���Ѥ��ФF�T���q�v�A��ť���z�]�ɤF�@�ǹq�v�C�b��и̦��\�h����۪��}�ܡC�ڻ{���A�q�v�O�����ɪŭ���A�ӳz�L�v�����ϴ_���M���@�ǽ��^���N���C�ڷQťť���i����q�v���ݪk�C
�]½Ķ�^�A�����D�O�b�ݤ��i���Q�z�L�q�v���F����A�٬O�z�L�q�v�o�شC���Q���ɤ���H
�ݡG���i���Ʊ�z�L�q�v�Ǽ���k�ܡH�αz����o��߷R�q�v�H�z�Q�ιq�v�@���u��ܡH
��: ���A���A����S���A�ڤ��Q�o�C�p�G�ڪ��q�v�o�F�@�ǹﴼ�z�B����Φ�Ъ�����A�ڷ|���@�O��q�v�����Q�C�ڤ��Q�G�ѻ��ڪ��o�ǥ@�U���B�M�������ʳ��M��Ц����C���O�A�O���A���M�C��Ƴ��i�H���@�Ŵ���Ъ��C���C�u���T�˪F�褣�i�H���@��Ъ��C���G�ˮ`���ߡB�g���M�����C�u�n���n�G�ơB�u�n���ƨ��@�N���@�Ǻƨg�Q�k�����̡A�ڦ۵M�ַN��ǹq�v�C��ثe����A�ڹ��`�W���ʧ@���B�R�����Bù�ҥv�B�T���l�v���q�v�S������C�i�O�A�֪��D�O�A�ڤ]�i��|�C�����@�ӹq�v�H�A�b�y�����n�t�ɺt�|�P�N�ڡA�ר�O�s�@���ߪ��q�v�B���ߪ��R�O�@���H�A�ڭ̪��ͬ��������M���[�����f���C���A�Ѧb�h�Τu�@�F�@�Ѥ���A�A�u�Q�ݤ@��²��B��E���q�v�C�������A�]�Ьݤ@�DZ����������G�ơC
�b�q�v���@�ɸ̡A�ھǤF�X��ơC��Ы�Q�M�q�v���Ǭۦ��A�ڤ��O�b�ͭ��Ǫ������C�����W���ܦh�H�誺�q�v�A��F�X�ʸU�A�M�ᦳ�H�N�|�ݡA���ǤH����n��o�ǦH�誺�q�v�C�]���ڭ̬ݳo�ǦH�誺�q�v�ڡI�o�N�O������C�Ҧp�A�����W���ܦh�Z���B����ƪ���ЦѮv�A������H�]���H�̳��w�L�̡A�ƹ�W�H�̳Q�L�̧l�ޡC�ӥ����W�S���h�֦n�q�v�A�]���S���ݨD�A�ҥH�S���ѵ��C
�ݡG���i���A�A�y�������h�ìO�q�F��k�̦n���D���C�i�O�b�m����g�n�����줣���O�A�ڭ̤��Ӱ��۩����@�ӷ��ݡA���ӿ��椤�D�C�i�O�p�G�A�l�D���D�A�o���]�O�@�ذ��۶ܡH
���G�ڷQ�o�N�O���ͥͪ��ɮv�ܱo���n���a��F�C�o�N�H�@�Ӧn���ɮv�i�H��ij�A�A�A���ӥ�Ū�����ѡC�]���ڭ̥u�O�H����ܡA���ɧڭ̷|�b�ɾ��|�������e�A���ݨ�@�ǰT���A���|�O��a���Z�H���A�]���@���A���D�F�Y�ӰT���A�n�ѱ��N�����F�C�o�M�ιq�����P�A�A�i�H���ɮקR���C�ҥH�p�G�A�u�O�ǰ|�����ǥ͡A���S���Y�F�i�O�p�G�A�O�b�l�M�@���F�ʪ��D���A�A�N�ݭn�@�ǫ��ɡC
�A�g�sĶ:��CĶ��
© ���������������v�Ҧ� | ��ICP��09053241�� | �ʤ����w��1101084005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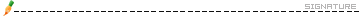
![ip�a�}�w�]�m�O�K](skins/Default/ip.gi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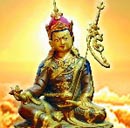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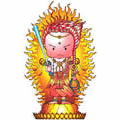


 �v�Ĵܭ����i��
�v�Ĵܭ����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