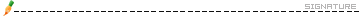證悟的雲水行者
紐修堪布仁波切生平自述
這一點也不是什麼修持者的傳記,它只不過是一連串苦難的記載罷了!
我於一九三二年誕生於東藏。我的父親是一位打家劫舍的綠林大盜,他打傷人、劫財甚至取人性命。由於我在很小的時候,我的父親便棄家而去,所以我對他的印象並不深刻。他就像我們在西部牛仔片裡常看到騎在馬背上的歹徒一般,習慣性地在東藏與西康交界附近的叢林中出沒。
我家裡有三位男孩,七位女孩。我的兩位哥哥長得像父親般魁梧,所以我父親很喜歡他們。
在三位男孩中,我年紀最小。由於我的身材比較瘦弱,所以父親常常奚落我,說我像個女孩似的,一點用都沒有。我的父親經常教小孩打鬥,由於女孩子們和我都不喜歡打架,所以父親便不理會我們。
我的母親是一位溫柔婉約,充滿慈愛與容忍的女性。雖然她必須撫養許多小孩及處理繁雜的家務事,但她對修持教法具有無比的虔誠恭敬心。因為我在慈愛與溫和的特質上與母親相似,所以她對我在教法的修持上寄予深厚的期望。我的母親對將一生奉獻給家庭,知道因果的道理及念誦祈禱文便已感到十分滿足。
我父親的母親,也就是我的祖母,她也是一位虔誠的佛教修持者。她的上師是巴楚仁波切的心子──偉大的大圓滿上師紐殊龍多天北寧瑪。她雖非博學之士,但她對所接受的教法非常熟練,藉由修持之力,她能了解所接受的教法,並因此轉化她的內心相續。
她恆常祈願她的兒子能迷途知返。
我至今仍然記得在我還在很小的時候,我母親及祖母手搖著搖籃,對著我唸道:「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
她們也會一起唱誦祈禱文、相互談論佛法並向紐殊龍多天北寧瑪殷切地祈請。
雖然她們不知上師當時在何處,她們總是熱切的盼望上師能現前給予教法並加持她們。她們總是互相地提醒彼此這位上師是多麼多麼地偉大。這便是我第一次聽到這位偉大上師的名字──紐殊龍多天北寧瑪。
這個名字至今仍然是我無上的激勵之源。
當我稍微大些時,我的祖母便告訴我紐殊龍多是她敬愛的根本上師,並訴說上師是如何地給予她新的生命。
雖然她在經論上的研究不多,但是她對大圓滿的修持有深厚的經驗,並喜愛修持菩提心的教法。她終其一生念誦六字大明咒達三億遍之多,且不斷修持慈悲心、菩提心的禪修。
我的祖母跟我說,既然我的個性溫和、善良,我應該走上母親那條修持的道路,而不要學我父親。她甚至進一步勸我去找一位充滿慈悲、菩提心的好上師,好好地在他的坐下聽聞、思維、修持,以達到同上師一樣的覺悟智慧。
她說這是佛陀的告誡。
在之後的三年裡,我負責照料家裡所蓄養的禽畜及一些稼穡雜事。雖然在這段時間我沒有學習任何教法,但是我心中始終惦記著這位偉大上師的名字。
在我五歲時,我的母親及祖母帶我到附近一座薩迦派的寺廟裡去,在那兒的僧侶們剪了我的頭髮,並給我一個皈依法名。
這座寺廟約有一百名喇嘛,廟裡的住持是我的舅舅,他的法號為蔣揚肯帕特祈。
《早年的寺廟生活》
由於這層親戚關係,寺廟住持特別關照我。我立即開始學習讀與寫,這對我而言十分容易。
但並不是每個小孩都有這樣的機會。
要住在寺廟裡當個沙彌,我們必須每天到村落去托缽行乞。至今我的腳上仍存著當年沿門托缽行乞時被西藏獒犬咬傷的疤痕。
當年少的小沙彌太頑皮時,他們不僅會挨打,還會在寒冷的冬夜,被罰坐在戶外受凍。這些可真是苦日子啊!
在我十歲時,我的工作是照料寺產所擁有的上百隻羊。牠們偶而在寺廟範圍內活動,偶而必須趕牠們到寺廟外的草原去吃草。
當天氣好,陽光普照時,我就會特別輕鬆、快樂,只要看著羊津津有味地吃草便可;但是當下雨,天氣寒冷,颳風下冰雹時,我將連擋風避雨的地方都沒有。
再者,我不能眼睜睜地看牠們走失在深谷濃霧中,我必須到各個方向去趕牠們往一地點集合,並在天黑前趕牠們回寺廟。我很清楚地知道這一共有幾頭羊,我甚至知道每一頭羊的長相及牠們個別的名字。
在春天及為期極短的夏天裡,到處是鳥語花香。西康的風景在這段期間簡直是美極了!其餘的時間則通常是酷寒難忍的。
我至今仍記憶鮮明的是那風和日麗的夏天田園景象,羊兒只顧著在那兒吃草,我則渾身舒暢地平躺在陽光照射的草原上,注視著湛藍色的晴空,讓心鬆坦安住,不加整治。
這便是我自然、不捏造禪修進展的開始。
有時,身旁的鳥兒會聒噪起來,或者一些念頭會襲上心頭。
這時我會自忖道:
「我在這裡做什麼?聽這小鳥歌唱嗎?我為什麼會在這裡?
祖母告訴我世上唯一有價值的事便是修持與證悟神聖的教法。
雖然我已經進入寺廟,可是我一直只是當個牧童罷了。
我要如何值遇一位具德上師,追隨他並依教修持,而不只是穿別人穿過的破舊袍子,在這兒以牧羊消磨時光呢?」
終於我鼓起勇氣向母親表白,我想找到一位具德的證悟上師,追隨他,聽從他的指示實修的意願。我要知道所謂真正的神聖教法到底是什麼!
因此,我離開了這座寺廟到另一個山谷。
在那山谷住著一位真正的證悟成就上師──喇嘛立津蔣巴多傑。他是一位證悟大手印與大圓滿雙融的聖者。
在我大約十二歲時,我便在這位偉大上師的個別指導下,聽聞前行的教授 ,並開始圓滿五十萬遍的前行修持。
之後,我要求並獲得上師傳授我止觀雙運的詳細解說。
我依照實修的傳承,以大手印的風格來運用金剛乘的禪修要訣。這些實修包括有名的大手印四瑜珈──專一、離戲、一味及無修瑜珈。
後來,我慢慢地發現若我在經續教法,特別是珍貴菩提心的教授的聞、思沒有堅固的基礎,我在實修上便很難有實質的進展。
誠如經論上說的:
沒有聞思便逕行禪修,就像盲者欲攀登山巖;
若只有聞思而無禪修,就像斷肢者欲攀登山巖。
立津蔣巴多傑同意我的看法。
於是我便隨著寺廟裡精通經論且有修持證悟的堪布們學習經論。我必須學習、念誦,甚至在所有僧眾集合前背誦無數的祈請文、儀軌及經論等。這可真是沈重的負擔啊!
我學習了三乘的三種戒律,其中包括別解脫戒、菩薩戒及密乘三眛耶戒;我研學印度大乘先賢寂天的《入菩薩行論》,阿底峽尊者有關自他交換的修心教授及其他自佛陀及祖師們傳下來相關的三藏佛法經論教授。我能記下整個十三大部。
之後,我深入研習龍樹菩薩的中觀宗義、中觀應成派的辯證法、因明、般若、慈氏五論及世親菩薩的《俱舍論》等等。
最後,我研學所有一百零八冊的三藏原典──甘珠,及比這還多的印藏歷代祖師詳細註解──丹珠。
以這種解行並重的方式,我將尊勝佛陀的三乘顯密教法,研修精通無餘。
我非常勤勉地接受經教的學習與訓練。
在二十四歲前,我在特殊上師立津蔣巴多傑及堪布的座下,接受傳統培訓阿闍梨及堪布的訓練,並同時配合著利美實修傳承的禪修與瑜珈修持。
我至今仍然記得當時我是一個多麼稚小且孤單的孩子,在一個陌生且為各種人取笑的地方。我也十分感恩地記得我那無私無我的上師,在我十二年教理學習與實修的追求中,所展現不可思議的慈悲心及毫不保留的教法傳授。
《接受心要口訣》
在我十八歲時,我從我祖母的上師的轉世那兒接受了大圓滿心髓龍欽寧體心性見、修、行深奧、秘密的口訣教授。
這個教法根據根、道、果三者無二無別的殊勝妙理,揭示了佛法究竟了義的本覺,也就是我們內在的佛性。
我很快地對在修持且卻(立斷)及脫噶(頓超)時會自然呈現無二元本自清淨與自然大圓滿的大圓滿教法,產生不可動搖的淨信與定解。
當時巴楚仁波切的心子──紐殊龍多天北寧瑪在多年前已圓寂。
他的轉世已經被陞座並由他前世的弟子們,其中包括無能勝者──堪布雅噶教育之。就是在這位轉世紐殊龍多謝乍天北寧瑪傳授我殊勝教法時,我明見心性。所以他成了我的根本上師。
我及我的根本上師住在偉大寧瑪噶陀寺廟邊遠地區的紐殊寺,因為這個因緣及我的根本上師的關係,我的名字便叫做紐殊堪布。
我在許多恩師的座下得到所有從龍欽巴尊者及吉美林巴祖師傳承而來的殊勝教法。
我能將龍欽巴尊者的《七寶藏》、《三休息論》,吉美林巴祖師的《雍登措》──《覺者功德藏》,一部詳述寧瑪九乘教法的權威著作等熟記於心。
這令我感到喜悅!
祖古謝乍天北寧瑪傳給我殊勝的大圓滿心髓的口耳相傳要訣。
祖古謝乍天北寧瑪是堪布雅噶的主要弟子。
而具有神異智慧的堪布雅噶是修持深奧脫噶成就的大圓滿上師,也是印度大圓滿祖師毗瑪拉密渣的化身。
當我還很小時,我曾晉見堪布雅噶,並接受過他一些口傳教授。因為當時我實在是太小了,以致於無法在堪布雅噶身邊做進一步的參學。
所以我都是單獨地從紐殊龍多謝乍天北寧瑪處逐漸地接受源自堪布雅噶的教法。
堪布雅噶是一位自然散發出非凡威嚴,無比攝受力,與不可思議風采的聖者。
只要進入他的房間,便足以震懾住我們的我執與我愛執,無我與開闊的本覺心性便能任運地開展。
即使當時我還很小,我仍然記得我當時是多麼的感動。所以這就是一位真正佛法大師的真實風範啊!任何人都會對他非凡的修持成就及自然的德性光輝,感到驚愕與受到激勵。在這個世界上還能見到這麼一位「活著的佛陀」,是多麼幸運的一件事啊!
這位遠近馳名的堪布雅噶之所以名聞十方有幾個理由的:他曾在禪座上一坐三年,寸步不離。
當這位巍巍的喇嘛進行三年的閉關時,他能在這三年期間完全安住在一種稱為「讓脫」本覺清澈透明的境界中。在這三年裡任何人都無法看到他身體投射的影子。這是千真萬確的事!
因為他是真正佛陀在這地球上的化身或色身顯現,所以當堪布雅噶在進行這閉關時,每逢初十蓮師吉祥日或十五圓日,八吉祥圖案會自然地在他的身上顯現!
堪布雅噶有如此多不可思議的殊勝功德,而這些聽起來是難以置信的。但是他有許多獲得即身成就的弟子們,讚譽他的修持與功德就像那虛空般深廣!
甲札仁波切與拜羅祖古仁波切是當今所僅存堪布雅噶偉大的入室弟子。
依據大圓滿傳承的說法,每一百年毗瑪拉密渣會由心中化現出一位證悟的大圓滿上師於西藏,以弘揚佛陀聖教。
在十九世紀,此化身為蔣揚欽哲旺波;在上一世紀,此化身則為堪布雅噶。
堪布雅噶有上千位證悟心性的弟子,其中最重要的法嗣為紐殊龍多天北寧瑪。
他由堪布雅噶處獲得不共的大圓滿心髓的口耳相傳要訣,之後將之傳授與我。
這是大圓滿的精華,龍欽巴尊者與吉美林巴祖師的心要,這也是奠基於寧體心髓的證量教授,是我不共的傳承與教法。
在這殊勝傳承裡,一次只能低語傳授給一位弟子,而不公開普傳。它是極其稀有與珍貴的!我自己曾將之傳與我少數身旁的弟子。
所有這不共傳承的持有者與祖師們都證得圓滿徹悟的境界,展現許多殊勝的證量與功德。不像近代的喇嘛如我者,徒具這令人景仰的聖哲們的影子而已!那些證得虹光身的傳承上師們是連影子都沒有的。
現在卻連體弱多病的紐殊堪布,都自稱能傳授這種不共殊勝的教法。這是多麼荒謬啊!
在這不共傳承裡的解脫口耳教授不死甘露,就像是智慧空行母新鮮的呼吸。這佛法的獅子吼聲一千多年來,深深地為雪域的瑜珈修持者所讚嘆。
而近代只剩下像紐殊堪布般的幾條狗在叫而已。不只是如此,他們還厚顏地周遊列國狂吠,吃別人的食物,引起一陣喧嘩與騷動。
這真是太好笑了!
之後,我在寧瑪六大寺廟之一的噶陀寺度過幾年。
噶陀寺在西藏被稱為噶陀金剛座,其意為噶陀菩提迦耶──覺悟金剛座的意思。這擁有七百多年歷史的噶陀寺被視為第二個菩提迦耶。據說有十萬瑜珈士於此證得虹光身。另一個說法是由於噶陀寺比丘僧眾為數極多,以致於他們身上穿的黃袍竟將天空給染黃了。
在噶陀寺我的上師包括十二位偉大的轉世祖古;八位能將甘珠整套及相關重要註解熟記在心,且具足修持證悟的堪布;五位既不是祖古也不是堪布,但是經由他們的勤修而具有極高證量的喇嘛,他們默默地修持且是比丘僧團的支柱。
在接受上師紐殊龍多謝乍天北寧瑪許多心要口訣後,我便到一個山洞中,根據口耳相傳的要訣閉關一年修持拙火。
我持續我的研修至二十五歲左右。我在深山雪地修持拙火直至天上飄下來的白雲在我身旁四周融化。
另外,在一次密集訓練中,有一段時間我同幾位同修師兄在上師指導下,在森林裡就像是動物般無拘無束地修持大圓滿的前行教法。
我還記得當時的情景,生活自在、無拘無束,掙脫社會的傳統束縛與概念的限制,就像是古代的大成就者般!這真是我修持生涯的黃金歲月啊!噯嗎后!
每晚我都會在恐怖的墳場或屍陀林中修持「覺」──施身法,一種金剛乘中修持般若波羅密多的法門,來布施惡鬼及冤親債主。
在其他的時間,我通常會在狂風凜冽的的山嶺或古代傳承上師所加持過的岩洞內禪修,或前往聖地及成就瑜珈士、空行母曾禪修過似香巴拉般隱密的山谷處獻供或護持種種殊勝功德行。
我已經圓滿噶舉派傳承的那洛巴六法、大手印及薩迦派的道果、輪涅無二、阿努瑜伽與時輪金剛教法的修持。
我的上師印證我已經圓滿各階段的修持、就像過去的傳承根本上師們一樣地面見本尊,直接接受其加持、口傳與灌頂。
之後我雲遊各處,晉謁西藏各大教派其他二十四位我也敬奉為根本上師的覺悟成就者。
在那個時候,我知道我要追求的是什麼,我也知道要如何去追求它。我實修這些教法並實證之,因此我成為一位利美(不分宗派)的喇嘛,也就是所有藏傳佛教寧瑪、噶舉、薩迦與格魯四大教派共同的法嗣。
《遠離西藏》
因為時局不靖,我與一些法友們於西元一九五九年離開西藏。以致於我與家人及其他留在西藏的法友們失去聯絡達一段很長的歲月。直到西元一九九二年我初次重返東藏,我才和我久未謀面存活的兄妹們團圓。
在印度,我於許多偉大的西藏上師座下,其中包括蓮花生大士的轉世攝政──敦珠仁波切、文殊菩薩的真身──頂果欽哲仁波切以及活著的佛陀──第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處請求並獲得圓滿的傳承教法。
之後,這些上師們及其他上師,諸如錫度仁波切、貝瑪諾布仁波切(貝諾法王)、薩迦崔欽及奏千仁波切等,都邀請我成為他們寺廟中佛學院裡的堪布或教務長,以作育僧才及培養為人師表的堪布。
我至今仍恆常地向所有給予我教法的二十五位根本上師們祈請。因為即便是我們認識成千上萬的人,無論好壞,我們的根本上師是我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事實上,真正最震撼我的不是我的上師本身,而是自然大圓滿──「奏千」的教法。這些在我的經驗中是真正最讓我驚嘆與感到不可思議,也是我最慶幸與感激的。
我對於給予我教法的上師們永懷一種言語無法表達的感激。在這幾年中無論我身於何處,我都盡我所能地將這些教法傳給其他人,以回報上師們的法乳恩德於萬一。因為我堅信這個方法,也唯有這個方法才能帶來最深邃的利益。
我在印度獨居達二十五年之久,就像一位孤獨的老人,沒有積聚任何資財。
有時候會穿梭在紅衣喇嘛群中,有時會身穿印度聖人的橘色布袍或簡單的衣著。有時候我會在寺廟裡講經說法,有時我會沿著恆河畔,與印度修士在印度教會、茅蓬、披棚等處一起居住。這就是多變的夢幻人生啊!
我有時地位崇高,生活舒適;有時環堵蕭然,三餐不繼。然而,內在真理與安樂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富足與受用,也就是所謂的「法」才是我真正的安身立命處。
有時候我會給予包括許多轉世祖古的一大群弟子們灌頂。這時他們會將黃金打造的灌頂寶瓶放在我手上,我再將之放在上千位喇嘛們的頭頂上。有些時候,我則是一貧如洗,以致於在印度加爾各答的街道上行乞。這些無法預料的起起伏伏,誰能盡述呢?
人生就是像這樣,充滿了各種不測風雲與興衰起伏。它是如此的虛幻、無常、無法掌控與起伏不定。而且到最後,我們都會死亡。這是多麼地神奇呀!
這許許多多的經驗、回憶與影響──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不好的──就好像是各種不同的夢境一般。
我歷經千辛萬苦到達印度,在這途中我的許多同伴們不知去向且至今音訊全無,我不知他們發生了什麼事情。到達印度後,我們追隨成就者的腳步,在阿薩姆、不丹、大吉嶺及噶林邦等可尋獲衣食、庇護所的地方落腳。
之後有幾年的時間,我在多處低地的難民營及蒸汽火車上與許多人擠在一起生活。同時,我也在熾熱、充滿塵埃的印度街道上行乞。
多年後,出乎我意料之外地,我發現我乘坐噴射客機,在現代都會如針狀般的摩天大樓空調升降電梯中上上下下,睡在豪華飯店及現代起居室的毛毯睡床上,在餐館用餐或露臺處休息。我被伺候得像皇帝一般!
在七零年代的早期開始,我似乎有一種病突然發作,且幾近死亡。有些人說我是在噶林邦的某餐廳被人下了毒。我的神經系統受到嚴重的傷害,以致於我幾乎完全癱瘓達多年之久。
在這之前,我曾將許多深廣的教法與灌頂賜予喜馬拉雅山區許許多多的喇嘛、轉世祖古以及在家居士們;在這之後,我的眼力變差了,且腳也不利於行,我的手會顫抖,且似乎即將死亡。
在這段不幸、艱困的日子裡,崁楚仁波切(Gangyur Rinpoche)及其家人適時地提供我一切所需的照料。他們提供我他們在大吉領的一座寺廟讓我在那兒療養。來自立窩切廟(大山寺)的喇嘛索南托嘉在這六年裡不辭辛勞地細心照料著我。無論是在印度或之後的歐洲,他都是我最忠實的侍者。
不丹的偉大瑜珈上師洛本索南桑波建議如我能攝受一位佛母並修持長壽法,我的健康狀態會有改進(在這之前,我是一位比丘)。這位年邁且可敬的瑜珈士是聽列諾布仁波切前妻的父親。
在他的介紹下,我與單卻望嫫成婚,且事後證實她真的是完美的長壽佛母。之後,我們便在一起生活。
經過一段日子之後,我被送到瑞士接受治療。我在那兒一處大的西藏社區中與我的藏族弟子們共同度過幾年。之後,雖然偶爾會給予一些教法,但大部分的時間我是在法國西南部的一座寧瑪中心過了八年的隱居生活。之後,有四年的時間,我在法國另一處三年的閉關中心傳法。之後,在西元1984年,我的法侶單卻拉從不丹來到法國與我會合。
自從那個時候開始,我的健康狀況便有明顯的改進。我比以前更積極地投入弘法利生的事業。各大教派的許多佛法中心不斷地邀請我,也因此我便應邀到世界各地去弘揚佛法。
單卻拉與我曾兩度重返西藏:第一次是在西元1990年,我隨著欽哲仁波切及其隨從返回西藏;第二次是在西元1992年,我隨著貝諾仁波切再次重回西藏,這次我得與家人團聚。現在,我正積極地重建三座寺廟及在康區設立幾間小醫院以利益當地居民。單卻拉與我定居在她在不丹──喜馬拉雅山區唯一獨立的佛教國家的首都辛布的家中。
《如夢似幻》
人生不就像是電影或是在浩瀚、虛幻海市蜃樓裡一連串的夢境嗎?我怎麼可能記得住所有從孩提時代是康區一位目不識丁的頑皮小孩,到現在變成一位頭戴老花眼鏡,白髮蒼蒼,滿臉皺紋且是能說善道的流浪漢之間如飛鴻雪泥般的陳年往事呢?這是多麼令人吃驚的一件事啊!我的人已老,背已彎。多麼神奇呀!一位目茫茫的年邁西藏觀光客,像劉姥姥進大觀園般地踏在外國土地上。噯嗎后!妙極了!真是太不可思議了!
面對這些幻化無常的種種經驗,除了視之為業力因果無欺的展現外,我們可有其他解釋?而這些業是誰創造的呢?除了我們自己之外,還有誰?
當我們認識到是我們自己造作了一己的業,而因此願意為自己無論是好、壞、順、逆的種種經驗負責時,這種正知正見不也讓我們能遠離憤恨與埋怨,且會帶來一種寬廣的自主性與責任感;同時對那些因為不具足因果知見而造業受苦的人們,由然地生起一種慈悲心?
或許由我來談論個人今生的種種遭遇並沒有多大的意義,但是這會提到我親身品嚐過的神聖教法,而這些教法確實是在動盪的時代裡,讓人內心悅樂的真正原因。教法的展現是不拘形式的,但是它們的共同內涵是一種偉大的休息與安詳。
事實上,我只是一名無足輕重的小人物罷了!我唯一的興趣與志願是服務、幫助他人,並護持與弘揚佛陀的教法。我完全沒有甚麼特殊的任務或工作有待完成,但是我確實感覺到既然佛法對我的此生有這麼大的利益,我很願意將我的經驗提供給任何對教法有興趣的人。
我希望在將來這神聖的解脫教法能廣為弘揚並平等地利益所有人類。我不是一位譯師,所以我沒有辦法以西方的語言來與西方人士溝通;我只是盡我所能以各種方式成為「法」的代言人。
我很高興見到現在有許多的西方人也對佛陀的教法產生無比的虔信,認為它不僅意義深遠且能提供實質的助益。
我一生中只了解一件事情,那就是佛法的妙善功德。因此,我很高興能見到他人與我有相同的看法。並且我相信只要他們能將之付諸實修,具足正念正知,他們一定能從深廣的佛法中獲得法益。
能夠了解此唯一,如萬靈丹般解脫一切痛苦與纏縛的自生智慧豈非一件大事?我們何勞永無止境地向外追求無法帶給自他究竟利益的種種世間繁瑣學問呢?
即使是在巴黎或倫敦的地鐵,我曾見到許多根性很好的非佛教徒,如果他們能蒙明師指導,是有機會在剎那間證悟無二元心性教法的。現在正是大圓滿來臨的時刻!它不是透過一種文化或學問來傳達,而是仰仗心靈的自然親切感與業果的成熟。
最近我碰到不少無法對表面的宗教活動感到滿足,因而誠懇地追尋真正實證之道的西方法友。我對此感到欣喜與受到鼓舞。他們願意傾所有心力投入在教法的研習與修持上,甚至為了能使心性開顯,願意做許多的犧牲。這些不就是教法興盛的徵兆嗎?教法除了自己內心之外,可有他處可覓?
如吉美林巴祖師的殊勝龍欽寧體上師瑜珈──體果嘉稱伏藏儀軌的起頭有言:
上無諸佛 下無眾生 超越存在與不存在
本具覺性的本身即是絕對的上師──勝義諦
自然安住在此本自解脫與圓滿的覺心 遠離執著
我皈依及發心
吉美林巴一般的持明者成就大圓滿上師,確實藉著大圓滿法成就佛果。雖然他本身並沒有在經論上下極多的工夫,但是由於他智慧輪的開顯,他能自然地寫下許多極珍貴的論著、取出龍欽寧體的伏藏並廣傳教法等。他的法教即便是在近三百年後的今天,仍然是我們在菩提道上的一盞明燈。
我本身並未成佛,我連在這輩子的將來與來世會在哪兒都不知道。但是這些都不重要,一點也不!無論發生甚麼事情,那些都已發生,而且一點都不需要擔心。
我只是對上師、教法與佛陀感到無比的感激,並殷切地盼望所有眾生都能與我分享這種加持與功德。而這些原本是屬於每一眾生的,無一例外。所以我不斷地祈願所有眾生能藉由種種的方便善巧,與此殊勝的教法結下吉祥的因緣。
願所有的眾生都能在內在大圓滿的光芒中覺醒,獲得圓滿的自在、安樂與成就!
沙爾瓦 孟噶蘭!願萬事吉祥圓滿 願虛空世界充滿和平與安樂!
(吉祥圓滿)
http://www.hwayue.org.tw/tergar/offering_plan_03_1.htm
http://www.hwayue.org.tw/tergar/offering_plan_03_2.htm
本文原載於『白玉法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