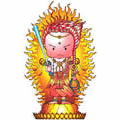.
.
安德魯·寇涵(Andrew Cohen)對宗薩蔣揚欽哲仁波切的專訪
Enlighten Next Magazine: Issue 31, December 2005–February 2006
http://www.enlightennext.Sorg/magazine/j31/dzongsar.asp?page=1
Enlighten Next雜誌第31期,2005年12月-2006年2月
寇涵:同時,你在電影裡說你是個殺手,那是你的工作。
仁波切:是的,以我身為學生的老師來說,那就是我的工作。然而,我並非承諾我有能力這麼做。你瞧,我是很喜愛世間八法的。我就像那些送到黑手黨家族裡的臥底警察,理應要仔細偵查那些人,卻愛上他們所做的事,因此我遵循他們所想要的。很難。那來自對於世間八法的貪執――貪愛稱譽,懼怕批評。
寇涵:然而有些最偉大的西藏上師是因極爲凶惡而聞名,例如馬爾巴。他是最凶惡的。
仁波切:對,當然。他們能這樣做是因爲他們沒有自己的規劃議程。他們唯一的規劃事項就是要證悟。他們不在乎其他人說什麽、想什麽――我把這個叫做CCL(Couldn’t-care-less;全然不在乎)。那具有最大的力量。但是今天誰有呢?沒有人。
寇涵:在電影揭露關於你的事情裡,最有趣的事情之一就是並列出你所扮演的各個角色。身爲在西方的上師,你與西方的學生一起工作,至少在理論上他們來你這裡是爲了證悟,然而他們仍是來自這個對權威向來不信任的後現代環境。而在不丹,數以千計的不丹人却毫不懷疑地確信你是個活神仙。
仁波切:我想我在兩塊大陸 (PS:亞洲和美洲) 都僞裝得很好。我去不丹時,知道要爲他們做什麼,知道做什麼是最和諧的。因爲假如我在不丹或西藏做或說我在西方說的東西,我會陷入麻煩。那就是我先前所指的,我這樣做是因爲我不想喪失弟子,我不想受批評。當然,我能夠合理化這些行爲,說是:「哦,它起於一個善良的動機,因爲我不想要危害數百人的修道。」
寇涵:你在電影裡說到很難與衆多不丹信徒建立真正的關係,因爲他們對你的那種崇敬。但是你的西方弟子們卻有根本的自我立場,覺得「沒有人比我更崇高」。而這也帶來困難,因為任何真正的上師若要幫助學生開悟,就必須從一開始就接受上師,明白一些學生尚未明白的事情。然後,當然還有老師加在自我、以及學生對自我的認同其上的巨大壓力。在〈真師之言〉中,萊斯莉·安·派滕清楚展現出你的西方學生裡有多少人在這個議題上掙扎――連同對階級制度與權威的看法,甚至還有他們對證悟本身的可能性缺乏信心等。
仁波切:對,的確。但是在兩種文化中有一個東西是類似的,就是「期望」這個罪人。在東方文化中,像是在不丹,可能有盲信,但全都有一個期望。在西方文化裡,他們也許保持懷疑態度,是世俗論者,但也有期望。那期望也許以不同的方式顯現,但基本上只有一個本質,那就是每個人都想要快樂。而這就是事情出差錯的地方。
身為佛教徒以及學佛,這和快樂一點關係都沒有。假如你學佛是為了要快樂,那麼就像是反其道而行,完全相反。證悟和快樂或不快樂都沒有關係。而這兩種文化來我這裡都是為了要快樂。那真是一切誤解的來源。
寇涵:是的。目標是要從快樂和不快樂中解脫。
仁波切:對,而我必須教導他們該期望什麼。不過這十分困難。
寇涵:置身於兩個不同的文化,這似乎對於你要做單純且真正的自己造成挑戰,因為一方面在不丹你需要扮演一個特定的、你已接受的角色――那是你要遵守的法則,是你的命運。但是在傳統情況下有某些相關的限制。而在西方由於後現代的俗世情境,也有許多限制。因此,你想單單做個完整且自然的自己,甚或是做為老師或上師,這樣的能力必然在兩種情況下都受到禁制。你能對此稍談一些嗎?
仁波切:這是個非常好的問題。這全都在告訴我,底線就是我需要發展出自己的勇氣――去學習「全然不在乎」的勇氣。早晨,帶著些微良善的發心,我能開始傳法,我確信那會累積一些功德。至少我不會四處遊走,教導人們把自己炸了或是殺掉異教徒。而即使是傳法,我也只有在心情偏向靈性方面時才會做。不過現在我的工作,我的職責是要先發展出自己的「全然不在乎」。至少我需要去學習全然不在乎,我需要做得到。然後,即使我在西方得到不良風評,我也完全不在乎。一旦我做到了,那麼我就達到一定的境界,具有真正的慈悲。在那個時刻之前,一切都有些虛偽矯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