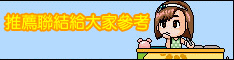�p�X�s�D��
�sĶ�����ʡ�����
2020�~3���9�� �W�� 06:24
�ڬw���A�D�J�����M���A���X�~�e�q�H�D�D�q�X�o���ǤW�ʸU�������ڷ��A��~�����F����Ī���������J���j�w�߳��A�ڷ��P�g�ը�B�Q��ȵ������ӷ��añ�p��ij�ê������A�p�P�N�����F���u�~�]�v���o������A�p���D�g�ը�H�}�������i�J�ڷ��n�١A�]�P�ϳ\�h�����b�Q��ȳQ�H�D���θj�[�P��d�A�ƦܾD���ŦD���`�C
�^��ó����ɡA�ھڤ@���~�����ڷ������Ƨѿ��A�ڷ��ӻ{�j�[�����p���b�Q��ȬO�u�@�Ӧ��Q�i�Ϫ��ӷ~�Ҧ��v�A�\�h���L�P�H�f�c�l�ۺٮ���ĵ�ö��A���N��d�����ӡA�H���o�ڷ��������u�g�O�v�C
��گS�j��´���ܡA�b�Q��ȡA������U�W�����D�F���B���L�P�Ǹo���θj�[�A�䤤�\�h�H�D��ŦD�M�h�ݵ����H�D�覡��ݡA�Ӳ�´�ë��ڬw�F���O�@�ǡC
���F�Q��ȥ~�A�ڷ��]�b�_�D��L��a�B�F�D�������Q�ȵ��u�D�w�����v��a�гy�X�e�j���j�[�P��d���~�A�ٸ�Ĭ���e�W���̡B�D��ڦD�ƪk�|�H�Ԫ��o�_�D���ڧƺ����y�F����ij�A�ڷ��ٴ��M�bĬ���F��a�϶i��رڱO�������L��´�u�M�L�Ρv�X�@�A�o��ݼɪ����L�{�b�ۺ٬O�u�ֳt�䴩�����v�A�����ڷ��l�������C
�S�H���D���h�ֲ����D�o�Ǽڷ���U���Z�O���`�A���O�L�h���~�A�q���̤⤤�k���������A�ܤ֦���U�H�b�a�������šC
�����٫��X�A�ڷ��F�������Ѥ]���ܼڬw�H�ﲾ�����A�סA����þ�ﲾ���߳��N�]���q��Ӫ��P���ܬ��Ϲ�C
���~�A��þ���O�ڷ�������A���]���ڷ��a�z��m��t�A�ڷ���ݧ�þ���A���ݧQ��Ȥ@�ˡA����̻��A�ڷ����G�Q�������ɥi��d�b��þ�o�Ӽڬw��t��a�A���n�i��ڬw�֤ߦa�ϡC
��þ�ܴ��մ��q�e�����먽�ջ��A�ڷ��@���u���ڭ̷P��L�U�M�t��v�A���G�N�O���a�����������쥻��������O�A���ܬ�����C




2020�~4��22�� �W��9:00
�����`�Τt�����]22�^��b�ծc�̱��O�̷|���ŧG�A�Nñ�p�@����F�R�O�A�Ȱ��ֵo�U�١u��d�v���u����X�k�ä[�~�d�ҡv60�ѡA���L�u�@ñ�Ҥ��b�o����F�R�O���C�]���f�ݳ��ɡ^
�t��20����M�b���S�W�o��A�b�ثe�o�ӫD�`�ɴ��A���F�O�@�u���j���ꤽ���v���u�@�v�A�L�M�wñ�p�@����F�R�O�A�Ȯɤ�����걵������~�겾���C�ɹj�@�ѡA�L�˦۫ŧG�o����F�R�O�����餺�e�A�N�O�Ȱ��ֵo��d60�ѡC
�t�����A�o���s���I�u�|����Q�n�b����M�D�ä[�~�d���H�A�Ӥ��O�Ȯɦb����u�@���H�C�]���A�u�@ñ�Ҥ��b����C�t���]���A�ثe�L�����Ȥ���O�n��U���~������H���u�@�A�Ӥ��O���~�겾�����N�L�̡C
���C����ɡA�t���o��z�S�n�Ȱ��������i�J���ꤧ��A�o���֤j���~�ϼu�F�t���]���h���A���u����ֵo��d�A�w�g�����u�@ñ�Ҫ��H���b����C
�o����F�R�O����B�Ĵ��O60�ѡA����|�A�ݬ��ꪺ�g�٪��p�M�w�O�_�����C




����A���g�O�h�֥@�N�B�h�ְ�a�H���ߥؤ��������Ѱ�C�Q�C�@���M�Ю{�b�ڬw����v�Э��`�A�f������ḹ�A�h��ۺ��Ī����w�P�Ʊ�A�Ө���w�j���M��s�ͬ��C���U�Ө�B�T�ʦ~���A�h�֦b�ڬw���Ũ�פU½���F�����H�̡A��a�a���B�a�ۺ��h�Ʊ�A�Ө���w�j���o���������šB�u�ݥI�X�K����ì���s�@�ɡA�ڷQ��n�����ӡC
�b�������F��@�ɡA����P�ˬO�h�֤H���ߥؤ����Ѱ�C�Q�E�@���A�����O�麥�I�ѡA�Ԫ��B�ȯ��W���A�n��u���\�h�H��ť�D�b�ӥ��v�������Ӧ~����a�s����A�R���L�������|�P�Ʊ�A��O�_�۩R���j�����M�I�A�b�ӥ��v�W���B���I���Ӧh��A�i�J���w�j���A�Ʊ�Ө�@���i�H�w���ߩR�����\���a�C�o�ǤH��}�l�q�Ʋ^���A�����q���q�v����֡A��ӾQ�ؤӥ��v�K���A�t���ǤH�h�}�]�\�]�B�}�]���f���B�~�穱�A���M���m�I���A���C��i�H�H���^�h�������a�m�A���a�H�b�a�m�_���ӡB��n��B�ɨ����A�Ĥl�i�H���Ш|�A�A�W�]�̤��p�~�C
�ܥ@�������ĤG���@�ɤj�ԲפF�A������ܾԳӧQ�A�쥻�H���w�w����l�ש�Ө�A���O��@���ԡB�s�e�ܦ�A�j��`�Ȧ@���Ҫ��H�ΰk�쭻��B�ΨӨ�x�W�C���O����P����j���g�a�۳s�A�x�W�P����]�u���@�����j�A�o����o�F�H�̤ߤ����Ѯ��ߡH��O�j�宣�@�������~������C�P�˪��A�b���ɰ���ҬF�����v�Ϊv�U�Ҳ��ͪ��W���H�h�k�`��A��O�H���ꬰ���I�C�]�����y�A�u���ۥѥ��D�S�Z�O�j�j������A�~�ണ�ѤH���w�~�ַ~�B�ۥѫO�٪��ͬ��C
�M�ӡA����{�����b�W�t�����|�Ĭ�A�����Y�v���ֽ����ڭ̡A����G�G�������{�M�F�@�Өƹ�G����ܦn�A�����רs���O�ڭ̦ۤv����a�C�H�����~�����t���A���O������ۡA�u�]���۶��Y�v���ֽ��A�\�h�w�b����ͮڦh�~�A�a�x�w�}�K������ĥ|�B�Ĥ��N���ظǮa�x�A���w���|���_�l�B���H�̶����D���A�o���³Q�պؤH�����~�H�A���{�ۡu�û����~��H�v���B�ҡC
�H�ͦb�@�A�D�����~�G�O�@�@���w�C�����ؤH�A�o�����o�˪��M�M�V�V�B�y���A�K�A�u���M�䨺�@���@�~�緽�B���\���a�A�̫�o���M�u�L�B�O�ڮa�v�C����@�E�C�K�~�ﭲ�}��A�H���ұo��ۧﵽ�A���O�I�_�Ӫ��H�s���A���۷�������Ҥw�g�Υ��b�ӿ첾���C�F�褧�]����A�ܦh�~�e�^�k�e�i�H���j�|�����^��B����B�[���j�F�ܦ~��A�H�̤��Q�����A���߰ݲ����ӥx�W���H��½���W�[�C�ڭ�ź�ƪ��x�W�A���̬����H�ߡA���i�B��������~�A���������������è�סA���״I���H�����N�A���n�s�B�n���B�n�̡B�n���A���C�~�������֮`�ȥ��Ӫ��H�̿�ܲ����C
����ɭԡA�ؤH�~��u���֦����H�̦w�ߩ~���A���ΦA�Q�۲����L�ꪺ�n�a��O�H����ɭԡA�ؤH�~��u���֦��ۥѥ��D�B�ͩR�]�����ҫO�١B�B�ݩ�ۤv���n�a��O�H�S�O����ɭԡA�ؤH�~��u���֦����ΦA�`�ȾԪ��B���ΦA�`�ȥ��h�ͩR�]�����n�a��O�H
�⩤�T�a���F�����Ӧn�n�Q�Q�C




�ڭ̷Q���A���D���O
���^���F�@�Ǭݦ�²��o�����T����y�^�������D�C�x�W�k�O���S���O�ٲ��u�H�L�̬����ӶD�H���u������n�k�]�H�L��ı�o�x�W���n�A�����^�h�H�@�����u�B�ʤu�@�̡A�o�dz��O�ɱ`�Q�ݨ쪺���D�C
��G���q���]�x�W��ڳҤu��|��s���^
�C�үS��Ʃ��᪺�q���@�m�L�D���l�n6/28�_�P��b�����L�u�x���X�A�o���ӬO��~�ӡA�ߤ@�@���H���u���D�D�n�W�L�u�q���x���q���@�C�@�~�e�Ӽ@�s�@�b�e����Ʀ����Υг��լd�ɡA��TIWA���L�X�ݡA�@�~��ݨ즨�~���ܷP�ʡA�P�ʪ��I�b��A�Ӽ@�K��ƹ�A�����������СA�]�����X�@�Ӭ��n�����סC�H���u�@���G�ƥD������ƥͲ���~�Ӻ�O��tij�D�̪��D�y�A�q�@�����B�������B�p�@���ƦܥD�y�s�i�A���j�T�ϥβ��u�@���D�D�A���m�L�D���l�n���X�F���P���[�ݵ����A�@�Ӳ��u�u�ݡv�x�W�������C
�x�W�ثe��71�U�~�y���u�A�䤤�|�Q���U�s�y�~�B�G�Q���U���@�u�B�@���D�n�y�g���~�y���u�����@�U��d�H�A�o�s�H�ӥx�e�n���h�ɿ���I15-20�U�O�A���۶ŨӨ�x�W�A25�U���@�u�S���k�O�O�١A45�U�s�y�~�κ��u�����Ұ�k�O�١A���j�h�B��@�Ӧ��k�o�L���O�٪��B�ҡC�b�o�̡A�ڤ�����ͤӦh�k�O���D�β��u�B�ҡA�o�Ǥj�a�H�K�����N�䪺��@��s�D�C
��ܬO�������¦��
�ڷQ�ͪ��O�ڦb�@���@���ݨ쪺�R�D�G��ܪ�����C�Ӽ@�q�k�h���u����ۡA�P���a�����Ӿ�a�x���U�d���o���Q�������k�ʨ���p���A�ͤU���L���y�ĤG�N���l�[�������}�i�C��۸�p�����զX�O�ܦ��쪺�]�w�A�L�̳��O�o�Ӫ��|�۹侀�h�S������o�V�O�Q�L�o��n���H�A�L�̦U�ۭ���ܦh���D�A�q�ͦs�����U�]�p�泽�f�^�}�l�A�o�i�X���P�s���A�o�ӳs���S�A�^��ͦs�����U���̡A�i�ӵo�i�X���Q���|���ȱ������B�~�a�x�A�ͤU�D�B�ͤl�k�C�b�@���ڤ��_�ݨ�H����ܬO�ݭn�����¦���A�ڦ��h�֥����H�i�H�Ӿ�h�֭��I�H�ڸT���T�o�_���ѡH�o�Ǥ]�O�ڦb�B�z���u�ӮפQ�h�~���_�ݨ쪺�C
��ۦb�P��F�o�ͪ���Ĭ���ܸ����A�����]��۸��A�d�b��W���O��l�O��Ψ����F�X�k�u�H���n�o��¾�a�_�F�k��A��ܥH10�U�M�Ѧ^��F�l�[�A���h�����u�A�Ӧۤ����a�x�B���j�Ǫ��k�q�L���U�צbĵ��e���A�Ƶo�{�������u���ͫo�U�N�ѿ�ܰk�]�C�@���X�Ӭq�����b�i�ܿ�ܪ�������¦�A�ө��媺�a�x���p���L�����T�Ӻ��u�̭��A�̸T���_���Ѫ��@�ӡC�I�W¾�a�����n�A���M�k�O�W�w�o���v�Q�V���D�D�v�A���ֳ��o�L�����B�����D���G��¾�a�_��ΨD�v�L�{�H��ܦ^�a�ܤ��٦������i�������U�C�l�[���k�ͦ��}���S����o�������A�W�ۨD�ͪ����ͯʥF�䴩�����u���ܥ��]�A���C�H����ܱq�Ӥ��O�u����ܦӤw�A�ӬO�a�ۦU�ح���θ귽����C
�k�רä��i�����ɭ��٫ܦ���
���@�t�@�����ګܷQ���˵��j�a����]�O�A���^���F�@�Ǭݦ�²��o�����T����y�^�������D�C�x�W�k�O���S���O�ٲ��u�H�L�̬����ӶD�H���u������n�k�]�H�L��ı�o�x�W���n�A�����^�h�H�@�����u�B�ʤu�@�̡A�o�dz��O�ɱ`�Q�ݨ쪺���D�C��ۤ@�Z���u�����Q���������|�A�L�̬����ӶD�H�p���ͤU�l�[���������L����f�A���o���p���ܦ��L���y�H�y�H�άO�{��W�ڳB�z�L���ʫI�ӮסA���`�H�ɱ`�Q�ݨ�A�A�����]�H
�p��ۤ@�˪����u�A�b�Ұʲ{�������|�ܱ`�����A�o�ǤH���O����ӶD�A�ӬO�p��b����@�~�L�{���o���|���ҾڡA�ӶD�ण��{�w�H�k���\���o�ഫ���D�H�o�ǰ��D���L�k�T�{�A�����W�I���ūo�O��ڪ��A�ҥH�h�ƺ��u��ܧԭ@�C�p�����B�h���k����ͮa�x�A�B�z�p�Ī����y�����O�ͦs�Ĥ@�n�ȡA�k�����o�o�H�ɦ��X�~���H�����֮a�x�ͬ��A�n�ѨM���y���D�N�o����ۤv�O�p�T�C�Q�ʫI���u�H�A�k�ת��ܴN���έ��藍�͵����k�ߨ�סA�ν�çA�P�H�����k�x�A�ٯ�����ȿ��i�a�C�������e�����D�Χx�ҡA��ܤ@�ӹL�o�h���覡�A�]���ѨM���D�������A����k�װ��D�j�Ӧh�F�A�Ӱk�ݭn�ѨM�����D�A���۲{��o�i�ͬ��U�h�A�N�O�@�إͦs�����C
�o�ص����b�x�W���F���x���B���k�̡A�άO������|�]�ɱ`�ĥΡA�������u�{��ͬ����X�����c��d�A��ܥΦX�k�ʡB�i�B�z�ʥh���P���u�A�Q�ײ��uij�D�A�h�ƬO�q���G�X�o�A�Ƥ֥h�ݭ�]�ߵ��A�]�����s��]�ӧx���F�A��P²��h�F�C�C�~�}�N�`�e��A�x�_�����j�U�Ӥ��ӧ��H���|�o��ij�A�h�ƪ��o���O�����j�U���O���H�u�a�ӧ��A�o���Q�����u���b���̡H�β��u��h���̡H�@���l�[�Qĵ��L�d�����X�����ҡA��h��ĵ�Q�Ǫ��i���A�s���������D�l�[�O�ӥi���H�A�t�ܥH�ᤣ�νL�d�L�C�S���H��ѨM�L�����y���D�A�̫�ONGO���X�ӸչϸѨM�C�o�dz��O�@�ذk�סA�o���֦��Hı�o�i���C
��ҽ֬O�x�W�H���e�A���^������O�x�W
�l�[�b�@���Q�ݤF�⦸�A�Aı�o�A�O�x�W�H�ܡH���~���L�^�������D�A���j�᪺�L�S���^���C�ڦb�X�~���u�@�g��̡A�w�g�Ƥ��M�Q��ݹL�h�֦��A�A�O���O�x�W�H�H���������~�ҡH�O���O�x�W�H�q�Y����O�@�Ӱ����D�A�֬O�x�W�H���O���I�A�x�W����ݤH�~�O���D�ڥ��C
�x�W�z�L�N���u�������߲z�����A�ɦ��@�Ӷi�B�K�Q���ͬ��A�L�̦b�x�W�u��O�Ұʪ�����A�����@�ӤH���ͬ����P�H�U�o�Q�[�Ŧb����C�a�x���@�u�i�H�T�~���𰲡A���O�@�x���~�L�𪺾������U�x�W���|���ѯf�ݡF�@��¾�a���u�����v�A�k�|�|�n�D�H�L���y�a�������ӭp��A�n���L����O�j���_�b�V�n�C���u�i�H�Q�����B�Q���U�A������ϧܡA�����u��V�D�y�]�w���˻��A�x�W���|�N���������A����]�H���ӨӡC�Qĵ��E�j����������D�A�L�a�۰k�h�����ٿ�ܻPĵ���ϡA�o�ӭ�o���j��ĵ�����ĵ��ϥΤ����A�P�H���欰�C���x�W�ߺD�H�u�A�O���O�x�W�H�v�����ݰ����X�o�ɡA�m�L�D���l�n�h�O�n�^���G���u�������x�W�Υx�W�H�O����˻��H
�����\Ū�G
�x�W�C33�ӤH�N���@��O���u�H�g���q�s�}�l��IJ���uij�D���A�]�W�^
�d���s��G�d�H��
�ֽZ�s��G���ʰa




2022-03-11 00:58 �p�X�� / �Y�_�͡��F�v�j�ǰ�����s���߭ݥ���s��
�Q�J���Ԫ�����O�d�@�A�o�ʾԪ����Xù���`�δ��F�����������d�C�Q�J���H���^�i�W�Գ����d���A���M�ܨءA���]�|��ҬO�_�z�L�~���ġA�i�קK�ثe���x�ƽĬ�C�t�~�A�ظ@�ܫP�k���Q�J�����ƤQ�U�����ɡA��ڪ��|�]�������ת��P���C
���L�A�o�]��_�h�~�e���F�Υ_�D������J�A�j�����ڬw��a�ƥ��A���j�a�ݨ�P�O�����A�դH�������w��A�D�դH�����h���Q�����������зǡC�i�����F�������ܥu�n�O�k����ŧ�ΫXù�������̡A���i�T�w�Ӧ۪i��������C�o�Ӱ�a���O�h�~�ڵ��ӦۥիXù������ԧJ�B�ԧQ�ȤΪ��I�������ܡH
�H�Ϲ怜�d�����ۦW�����a�Q�`�z�����q�A���M�S�������W�z�U���ɤH�����w�߳��A���]���ܡu�p�����n�A�ڭ̷|���d�����v�A�o�ѤF�ۤv�L�h�Ϲﱵ�ǨӦ۪��I�������A�����e�L�̦^���Ǥh�Ϊv�U���I�����h�M�I�A�����������a�Q���v����Q�n�ӽЬF�v���@�������C�L���X�o��ӱ��Ҧ��ܤj���P�A�]�������Q�J�������O�X���F�ꪺ��U�C
�s�ۤv��H�b��ڥi��D��[�����O�[�Q���`�z���S�i�Ҥ]���o�۷��J���G�u�o�ǤH�O�ڬw�H�A�ҥH�ڭ̩M�䥦�ڷ���a���dzƦn�w��L�̡C�o�ǤH�o���B���L�Ш|�A�S���ڬw��a�|��ߧY�N���{���@�i�����C�v
�������ɡA�b�ꤺ�����W���Ҭy�ǡA�@�ǥx�W�����Φh�Τ�ť�D�C���M�A�ڬ���a�@�N�����]�Xù���J�I�Q�J���y���������A���o�糧���b���I���B���F�M�_�D�o���D�դH������A�۷��ƥ��A�T������ڪ��|�ݨ쥦�̹�ͩR���Ȫ������зǡA�]�ϬM�o�ǰ�a���رڪ[���C
�t�譱�A�\�h�[�ݦ��q�l�C��ά��ڳ��Ȫ��\ť�H�A�i��`�N�즳�O��L�h��ԧJ�Ԫ��B�ԧQ�Ȥ��ԩΪ��I���Ϯ��Ԫ��A�\�h�O�̳��ɦ��N�L�N���y�S�X�j�P�رڪ[���C�����L�Ԩƪ��ĤT�@�ɤH���A�P���ױj�P�A�U�C�X�h�N�O�嫬�a�رڪ[�����ɡC
�^��m�C��q�T���n�F�v�O�̫��n�o�˴y�z�G�u�L�̬ݰ_�ӫܹ��O�ڭ̡A�o�N�O�O�H�_���]�C�Q�J���O�Ӽڬw��a�C�����H���[��Netflix�B�֦�Instagram�b���B�b�ۥѿ��|���벼�A�åB�\Ū�S�g�f�d�������C�Ԫ����A�ȫ��X�h�a�M�������H���A���i��o�ͦb����H���W�C�v
���ۤ�ȹq����`�O�̨f�ȥ[��b���ɡA�u���M�ڨS�����q���N�A���٬O�������Q�J���ä�����ԧJ�Ϊ��I���@�ˡA���g�F�@�B�G�Q�~�Ԫ��C�o�O�@�Ӭ۹����������ڬw�����]�b���ڥ����Φr�D�`�ԷV�^�A�O�@�ӧA���|���ݩΧƱ�Ʊ����M�p���o�ͪ��a��C
��a�s�����q�O�̬_�Ѧ�Ԧb�༽�ɡA���ܡu�o�Ǥ��O�Ӧ۱ԧQ�Ȫ������A�o�ǬO�ӦۯQ�J���������A�L�̬O����{�B�L�̬O�դH�A�L�̻P�ڭ̬۹��C�v�k�ꪺBFM TV�O�̬쨩���ɯQ�J���ɪ��ܡG�u�ڭ̳o�ؽͪ����O�ԧQ�ȤH�k�����F����Ӱ�F�v���F���C�ڭ̽ͪ��O���o���ڭ̪��ڬw�H�}�����}�A�H�D�O�R�C�v
���F�v�H�����رڪ[���A�γ\����F�v�ت��A���Y�P�˺A�רӦ��������[���C��u�@�̮ɡA�o�N�O�ڲ`�k�T�B���H���ܪ������I




2022-10-02 01:07 �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