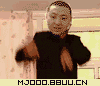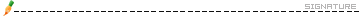資性朗悟﹐博學強記﹐讀書日誦千餘言﹐挽弓至一石五鬥─沒錯﹐這樣一個文武全才﹐英姿勃發的年輕人說的就是南宋高宗皇帝趙構。
趙構第一次在歷史這方大舞臺上露面很是激越慷慨﹕“靖康元年春正月﹐金人犯京師﹐軍於城西北﹐遣使入城﹐邀親王﹑宰臣議和軍中。”“欽宗召帝諭指﹐帝慷慨請行。遂命少宰張邦昌為計議使﹐與帝俱。金帥斡離不留之軍中旬日﹐帝意氣閒暇。二月﹐會京畿宣撫司都統制姚平仲夜襲金人砦不克﹐金人見責﹐邦昌恐懼涕泣﹐帝不為動﹐斡離不異之﹐更請肅王。”從這段描述可以看出﹐大敵當前﹐年輕的趙構還是很有勇氣和骨氣的。可從其中我們也隱約可以看出來﹐他的那位寶貝哥哥─只當了一年多皇帝的趙桓對他似乎不怎麼待見。明知弟弟在金營裏面﹐還允許將領們去偷營﹐這不是把他往死路上趕嗎。好在趙構命大福大─其實說來還是那句話─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裏。出了這檔子事﹐趙構還很鎮定﹐這使得金人心生疑惑─在他們看來這些長在深宮裏﹐只知聲色犬馬﹐錦衣玉食的王子哥兒在這樣的情況面前早應該是嚇得屁滾尿流了﹐而如果是親王的話﹐也太不把他當回事了。所以他們認為這個親王是冒牌貨﹐即使不是冒牌貨分量也不足。他們倒是猜對了﹐因為趙構雖是九王爺﹐可是在王室裏地位確實不高﹐因為他是庶出﹐而且徽宗對他老媽感情也不深厚。因此金人要求換人─因禍得福啊﹐趙構得以逃出生天。從以後趙構的表現來看﹐我想在這次作人質的過程中﹐他深刻的認識到了兩點。第一就是他看到了金朝兵威之強盛﹐使得他那點在深宮裏養成的不知深淺的“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壯志豪情深受打擊﹐也第一次深刻的體會到了現實軍事政治鬥爭的殘酷。其二是他可能也因此對老爸老哥有了很深的成見﹐並體會到了帝王家裏親情的涼薄─這也可能是他以後對國恥家仇不那麼刻骨銘心的一個原因。
過了不久﹐金兵第二次圍汴京─他又攤上了一個和上次一樣的苦命差事─去金朝議和。這次是金人指名道姓要他去的﹐可能是經過上一次他的表現﹐金國人覺得在宋室裏面還就他有點出息﹐所以要先抓過來。哪知我們的九王爺又一次因禍得福﹐還因為這一趟“出差”從此踏上了延續宋室香火﹐保存國祚的中興之路。
談論趙構﹐我們還是從這裏說起─他是南宋的第一個皇帝。在中國歷史上﹐一共有三個中原王朝因為內亂或外族的入侵被迫南渡﹐它們分別是晉朝﹑宋朝和明朝。在宋之前﹐是晉室的衣冠南渡。據史載高宗聽說楊萬裏的詩裏把他比成晉元帝﹐非常不高興。有些對趙構不感冒的人會說﹐晉元帝再怎麼不濟。也不比你趙構差─畢竟人家沒有向北方稱過臣。但我們還是需客觀的承認﹐高宗無論是個人在歷史上的地位和影響力﹐還是對王朝的建設和發展﹐高宗都是要遠遠超過晉元帝的。畢竟宋室南渡時的情況是要比晉元帝在建康稱帝時的情況艱難許多。這是因為當時金朝已經滅了北宋﹐並派兵對高宗處處緊逼﹐而他身邊兵馬很少﹐情況實在緊促。而晉元帝稱帝時在南方已經經營了近十年﹐基礎已經比較牢靠﹐同時北方很長一段時間陷在混亂之中﹐對南方的威脅比較小。其次是趙構即位時才20歲﹐沒有任何的政治軍事經驗﹐而司馬睿登基時已經41歲﹐在地方從政也有了20年左右。第三是司馬睿有王導這樣在江南根基深厚﹐深孚眾望的人輔導﹐而趙構卻缺少這樣好的條件。第四是﹐終南宋一朝﹐無論是從國祚的長久﹑皇權的威望﹑軍隊的控制﹑王朝最後的結局方式這些方面來考慮﹐南宋都是要強於東晉的。有些人會提出在晉元帝有王敦的叛亂─其實﹐高宗朝開始時不也有苗劉叛亂﹖當然﹐這樣的可比性畢竟不大﹐因為歷史環境不同﹐高宗和元帝的享國時間也有巨大的差異。
既然說到了王朝的南渡﹐我們不妨繼續談一下南宋和南明的情況。高宗被趕到南邊時﹐身邊親兵僅一千餘人﹐然而他通過各種方法﹐迅速調集人員防守住了江淮﹐同時建立了南宋的根基。相比於明代﹐有明一代雖然一直經營南京﹐整個南方的經營遠過於北宋對南方的經營﹐南京六部九卿設置齊全﹐官僚機構完備﹐且左良玉和四鎮軍事實力強大。而觀於甲申以後﹐南明竟不能守﹐史可法雖然一代忠勇﹐令人欷歔﹐但是在調停部署上近乎昏聵﹐四鎮頃刻土崩瓦解。與南宋相比﹐真是天差地別。以此論之﹐宋高宗雖然在恢復中原方面深受後人詬病﹐但也不能算一個昏君。
終宋高宗一生﹐我們都可以看到他是一個堅定的“和平主義者”。在紹興八年之前﹐南宋既和既戰﹐對“和”的追求並不那麼徹底。這裏面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趙構登基不久﹐需要一面旗幟﹐一個信念來團結廣大的抗戰軍民。如果這個時候一味求和﹐無疑會涼了廣大將士們的心─人家還不如擁護張邦昌呢。第二就是歷朝歷代無不是以忠孝治天下﹐現在父兄被人挾持到東北打獵去了﹐你卻一門心思求和的話﹐於國是不忠﹐於家是不孝﹐那麼得國就有些名不正言不順了。第三是金國那個時候壓根就不承認你這個“流動”政府﹐他們先後立了張邦昌和劉豫﹐對趙構這個小孩子是必欲擒之而後快。所以﹐在前期金宋兩朝是打打殺殺的鬧了好一陣子。後來金國人發現自己一時是滅不了這個小朝廷的﹐而這時宋高宗的地位也漸漸穩固了﹐再不必羞答答的表示自己的“和平願景”。
到這裏似乎可以進入人們熟悉的主題了─那就是八百多年來在這位君王世界裏最為後世詰責﹑嘆息和痛恨的兩個議題﹕和與戰﹐忠與奸。
小時候接觸的第一本書就是《說岳全傳》─一本章回體演義性質的小說﹐具體的樣子記不得太清了。因為那時沒讀書﹐是爺爺一回一回說給我聽的。在這本書裏─知道了那個歷史上最具悲劇性的英雄─岳飛。
談宋高宗﹐就繞不過岳飛─繞不過岳飛的為人﹑功業以及這對君臣之間的關係。
幾百年來﹐岳飛已經成為了我們這個民族的一個文化符號和精神圖騰。歷史上有兩個這樣的武將對我們的歷史產生過這般影響﹐一個是關羽﹐一個就是岳飛。關羽取義﹐岳飛取忠。不管王朝怎樣變遷﹐這兩個人都受到當政者的熱烈追捧─而且兩個人都神話了─都被封了“神”。尤其是岳飛﹐當年還是冤死在自己盡忠的統治者手裏─這樣的反差真是讓人唏噓不已。
根據史料﹐我們來總結一下岳飛﹕文武雙全﹐不貪財﹐不好色﹐為人耿直﹐堅持原則﹐對國家和君王赤膽忠心。但也有一些小缺點﹐那就是有時愛使小性子﹐說話辦事沒有足夠靈活性。當然瑕不掩瑜﹐千百年來人們敬愛岳飛﹐是因為他一直是站在廣大被異族壓迫的老百姓一邊﹐他所從事的是一項抵抗外來侵略和民族解放的偉大工作。所以不管歲月如何變遷﹐對岳飛的“崇拜”還將延續下去。
當然﹐我們也認識到﹐我們了解的岳飛─一方面來自民間的眾口相傳﹐最主要的還是來自一些史籍資料﹐尤其宋史。雖然在很大程度上宋史受到史學界的肯定﹐但是其中關於岳飛的傳記資料主要來源岳珂撰寫的私傳《鄂王行實編年》。一般熟悉歷史的人都知道﹐岳珂的《鄂王行實編年》對其祖有許多的溢美過譽的地方。這也可以理解﹐畢竟“遺老吊故國山河﹐商婦話當年車馬”。比如拿岳飛的功業來說吧﹐我們熟悉的朱仙鎮大捷在《鄂王行實編年》之前的史料中就不曾有記載─當然我這樣說也不是否定這次大捷的存在﹐只是存在疑問罷了。我們也可以參考一下金史─金史因為底本好﹐客觀性更強﹐史學界一般認為它比宋史要好。在金史中還是一些岳飛的敗績記載﹐岳飛的一些戰績也沒有今天我們了解的那麼輝煌。還有孝宗上臺不久為了北伐的需要﹐給岳飛平了反。但在其後不久(乾道二年)再下詔評定中興十三處戰功中(這次不用擔心功績故意被塵封吧)﹐岳飛卻榜上無名﹐這只說明他的殺敵功績被拂去若干年的垢膩沉積之後﹐在宋朝人之前﹐面孔依然比較陌生。岳飛是中興四名將裏面最年輕的﹐也是提拔最快的﹐而且他的地位和功績在當時就受到了肯定﹐我想這些大家都是沒有異議的。寫這些話﹐想說明的是即使我們非常尊敬這位愛國將領﹐但我們也無須把他的功業無限的誇大─因為岳飛的偉大之處不在於他的地位和戰績﹐而在於他那足可以穿越歷史長空﹐流芳千古的節操和錚錚鐵骨。
應該說﹐宋高宗於岳飛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岳飛是在常年的抵抗作戰中﹐被宋高宗所賞識﹐並一步一步從一個中低級軍官提拔為位高權重的高級將領。我們看到﹐自建炎四年(即紹興元年)岳飛第一次見高宗﹐到紹興六年的這段時間﹐宋高宗與岳飛的關係都很融洽﹐是君臣兩人關係史上的黃金期。其後宋高宗就慢慢對岳飛心生不滿﹐直至最後下定決心除掉他。其間是什麼原因導致這種關係的破裂─或者說是高宗對岳飛的印象急轉直下呢﹖
先來看看宋高宗與岳飛的關係﹐在早期﹐應該說宋高宗對岳飛有知遇之恩﹐而岳飛則事君以忠─如果這種君臣大義能夠維持下去﹐那也真是一段千古佳話。我們還可以看到﹐不但在國事上﹐就是在個人感情上﹐兩個人的關係一度都很不錯。比如岳飛有好酒酗酒的毛病﹐高宗就勸他戒酒。岳飛有眼疾﹐高宗就好幾次親派禦醫去給他治病。還有高宗對相馬之術深有研究﹐所以他有時還和岳飛輕鬆的論論馬。這些都顯示他們不但有君臣之義﹐還有朋友之情。
其實﹐這是很正常的事情﹐對於剛登基時的高宗來說﹐如果他也需要一位朋友的話﹐那岳飛可能是最合適的了。首先﹐君王的朋友﹐可能裏面或多或少的有政治意圖在裏面─每個人可能都這樣。對於高宗來說﹐他需要一個朋友﹐更需要一個有能力的嫡系將領。因為他那時可算是匹馬渡江﹐手裏的兵馬基本上都是臨時拼湊的─本來嘛﹐他自己從未帶過兵。而岳飛恰好可以充當這樣一個角色﹐有人會認為張俊是高宗在任河北兵馬大元帥的時候帶出來的。事實是在之前張俊就帶兵許久了﹐並不是高宗一手提拔的。而岳飛則幾乎是高宗一手培養的﹐要說嫡系﹐岳飛才是他的嫡系將領。第二﹐高宗就比岳飛小四歲﹐是當時所有大臣將領裏與之年紀相差最小的(其他除劉錡外﹐都比他大15歲以上)﹐不存在代溝的問題。這肯定使他有親切感﹐對於孤家寡人的高宗來說﹐這種感覺很重要。他是君王﹐他更是一個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何況他那時才二十多歲─這本是一個很容易衝動也很需要友情的年齡。第三﹐在岳飛面前高宗不但有親切感﹐應該還有安全感。你想高宗以前在深宮裏錦衣玉食﹐估計一點重活都沒乾過﹐當了皇帝後﹐整天被嚇得到處亂跑。可岳飛呢﹐比他大不了幾歲﹐年紀輕輕就要帶兵打仗﹐衝鋒陷陣﹐乾的可是有了今天就沒明天的營生。可即便如此﹐他照樣慷慨激昂﹐以天下為己任─他的鬥志和熱情一定感染了高宗﹐讓他感覺有希望﹐有安全感。第四﹐岳飛是那種耿直忠厚的人﹐這樣的人在開始階段﹐一般都討人喜歡─尤其是君王﹐誰不希望大臣將領們少些花花腸子啊─可是如果太少了﹐日子一久﹐估計自己也不喜歡─人性使然。第五﹐最為可貴難得的是﹐岳飛不但武藝好﹐諳熟兵法﹐而且還不是那種只知道帶兵打仗的赳赳武夫。他的文才還非常的好﹐還有更令他驚喜的是岳飛的書法也很不錯─書法這高雅藝術﹐可是老趙家的傳統手藝啊。和他老爸一樣﹐趙構是一個很有藝術修養的君主﹐他善詩詞﹐尤工書畫(想來有趣﹐在高宗﹐岳飛﹐秦檜這個南宋早期的“鏗鏘三人行”裏﹐雖然後來充滿血腥的鬥爭﹐但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長─那就是書法﹐這也和大宋的國策及文化政策有緊密聯繫吧)。所以君臣之間在國事之餘﹐還可以就興趣愛好切磋一下。
之所以寫這麼一大段﹐主要是試圖從另外的角度來審視趙構和岳飛這對歷史上有名的君臣關係。個人覺得﹐在歷史分析的時候﹐有必要加入人性分析。因為隨著歲月的流逝﹐環境和文化這些都會變﹐不變的是人性。而且歷史的主角是人─是人就有自己的喜怒哀樂這些情感─即使貴為君王也不例外。
寫了君臣兩人的關係﹐接著可以討論這段歷史上最有名的公案─高宗為什麼要殺岳飛了。
第一個原因廣為人知﹐即紹興七年三月﹐宋廷解除了“中興四將”之一的劉光世的兵權﹐高宗本來答應將劉光世率領的淮西軍隊撥給岳飛指揮。可是在張濬和秦檜的提醒下﹐高宗臨時變卦﹐拒絕將淮西軍隊交給岳飛。對高宗的出爾反爾﹐岳飛十分憤慨﹐一怒之下﹐他竟然離開本軍駐地鄂州﹐以為母守孝為名上了廬山。在封建王朝﹐未經皇帝允許脫離崗位可稱得上狂妄悖逆的大罪。在高宗看來﹐這種行為分明是要挾君主﹐但當時金兵的威脅尚在﹐解除岳飛兵權的時機並不成熟﹐因此高宗不得不再三下詔﹐對岳飛好言撫慰﹐敦促其下山。六月﹐岳飛返朝﹐向高宗請罪﹐高宗表示對其寬恕的同時﹐引用太祖“犯吾法者﹐惟有劍耳”的話以示警告。從這裏可以看出岳飛是個有點小脾氣的人─可是﹐即使“使氣”也得看對象啊﹐而且還要當皇帝的三次下詔來請﹐同時君王在這種事情上有自己的想法很正常﹐岳飛也算博古通今﹐這一點應該知道的。可岳飛不但為這個的事情發脾氣﹐還要當皇帝的三番四次來請﹐也可見岳飛認為自己和皇帝是有“交情”的─一般的臣子何敢有這樣的舉動﹖
第二就是關於岳飛向高宗建議“立儲”的事情。這裏面有兩個問題﹐一是在之前已經有大臣提過這樣的建議了﹐並得到了高宗的嘉許﹐為什麼岳飛一提出來他就不高興。二是立儲“正資宗之名”─歷史上就有是以高宗名義還是以欽宗名義立的爭論。我們在這裏暫討論是以高宗自己名義立﹐那無論從哪個方面考慮﹐高宗有猜忌憤怒之心都是可以理解的。首先從老趙家的傳統來說﹐是深忌手握重兵的武將干涉朝政的─尤其是立儲這樣的大事。其次﹐在高宗還只有三十歲的時候提出這個問題﹐他一般會朝兩個方面想﹕一﹑誰不想立自己的兒子繼承這份大家業啊﹐現在我沒兒子你卻提出來﹐分明是認為我不能生了吧。第二﹐即使不是第一種考慮﹐那麼立儲﹐還不就是為了安定人心﹐為出現萬一的情況做準備﹖難道我三十歲就會有什麼不測﹖如果是一般的大臣還好﹐那樣只會使高宗心裏不舒服﹐可能還要表面上稱讚幾句。可以岳飛的特殊位置﹐加上兩人關係還一度那麼融洽﹐提這樣的問題﹐就不簡單是惱怒的情緒﹐還使得高宗很難堪─任何一個男人面對這樣的問題都會心懷恨意的(何況他還是一國之君),哪怕他再忠誠﹐再怎麼替自己著想。
第三是關於議和的事情﹐本來對於國家政策﹐有宋一朝﹐武將都只有執行的份﹐可是岳飛不但不同意﹐而且公然反對﹐態度還非常堅決﹕“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善﹐恐貽後世譏議。”─這樣的話很重了﹐對於一心致力於“宋金友好”事業的高宗來說是很難接受的。
第四是關於岳飛兩次赴淮西的軍事支援行動﹐動作似乎都慢了一些。這是高宗臺面上要殺岳飛的一個重要原因。雖然關於這個事情有比較大爭論﹐但個人認為在這個軍事行動中﹐張俊需要負主要責任﹐但岳飛也是有一定責任的。
第五是宋金議和金國提出的條件﹐以前我覺得這個原因很可笑﹐很簡單─能戰方能言和﹐趙構也算是頭腦正常的人﹐怎麼會把敵方提出的無理條件認真的執行﹐這不是自毀長城嗎。其實分析一下就可以發現﹐這時宋朝基本上實現了以戰促和﹐雙邊大體上處於戰略相持階段﹐而且宋朝也不只有岳飛你一個能征善戰的將領啊。從另外一個事件中我們也可以看出來這個理由是正當的﹕1207年﹐南宋伐金失敗﹐宋朝被迫將主持伐金的宰相韓侂冑殺害﹐並將其頭顱送往金國謝罪。殺掉主戰派﹐以為和談信用─這是金國人提出的條件﹐應該是很正常的。我們還可以往下看一下歷史﹕1161年﹐金主完顏亮侵宋﹐宋金兩國翻臉﹐高宗禪位之後﹐第二年便從孝宗所請﹐為岳飛平反。這或多或少也反映了岳飛是和談的一個犧牲品─當然﹐原因不只這一個﹐裏面還有高宗的個人感情在裏面。
至於說岳飛北伐為迎還二帝的想法觸怒了高宗是經不起推敲的。第一是殺岳飛時徽宗已經去世多年﹐而欽宗呢﹐即使回來也根本就不會形成威脅。主要是因欽宗乃亡國之君﹐且當皇帝還沒有兩年﹐根基淺﹐沒聲望。那時南宋全是高宗帶出來的人馬﹐沒一點欽宗的勢力﹐誰那麼蠢會去討好一個啥都沒有的過氣前皇帝。
至於殺岳飛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謀反”﹐這個就不討論了﹐一是歷史上的“莫須有”已經給出了答案。另外﹐我們看到在秦檜死後﹐高宗還是給許多秦檜製造的冤假錯案平了反﹐可就是不給岳飛平﹐可是幾年之後﹐孝宗為了北伐向他請示關於為岳飛平反的事情﹐他還是答應了。從這裏可以看出﹐一是岳飛確實是被冤殺的﹐否則真是謀反﹐如果被證實了﹐在歷朝歷代都是滅族的大罪﹐何談平反﹖另外就是先前不予平反﹐後來形勢變了﹐又同意平反﹐可見其中有私人的感情因素在裏面─正所謂寵之越深﹐恨之越切。只是可憐岳飛﹐他的生和他的死都是統治者政治棋盤裏的一顆棋子罷了。
我們說岳飛冤死這應該是沒什麼爭議的﹐可歷史為什麼偏偏會選擇他呢。我們知道岳飛接近士大夫﹐又清廉自好﹐頗得軍心﹐能答出“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命﹐天下當太平”這樣的話﹐顯示出他是一個有遠大志向的人物。而雄心與野心常常是一回事﹐高宗對他逐步加重疑慮是很正常的了。我們了解宋高宗與岳飛關係﹐是否可以想到另外一對也很有名的君臣關係呢─雍正與年羹堯。岳飛與年羹堯都是文武雙全﹐為國之棟樑﹐也都是皇帝的嫡系人馬﹐一度和皇帝的私人關係也都非常好﹐為皇帝所倚重。可最後兩人都被自己效命的皇帝所殺﹐只是年羹堯沒那麼冤─畢竟他實在是飛揚跋扈了一些─而岳飛的“國際國內”形勢都複雜許多。
至於殺岳飛的是宋高宗還是秦檜─只能說他們都是主要凶手﹐不存在秦檜矯詔殺岳飛的事情--秦檜死後﹐有人攻擊他﹐高宗詔曰﹕“講和之策﹐斷自朕志﹐秦檜但能贊朕而已﹐豈以其存亡而渝定議耶﹖近者無知之輩﹐鼓倡浮言﹐以惑眾聽﹐至有偽撰詔命﹐召用舊臣﹐抗章公車﹐妄議邊事﹐朕甚駭之。自今有此﹐當重置典憲。”從這裏看出﹐殺岳飛絕對是出於宋高宗的真心。